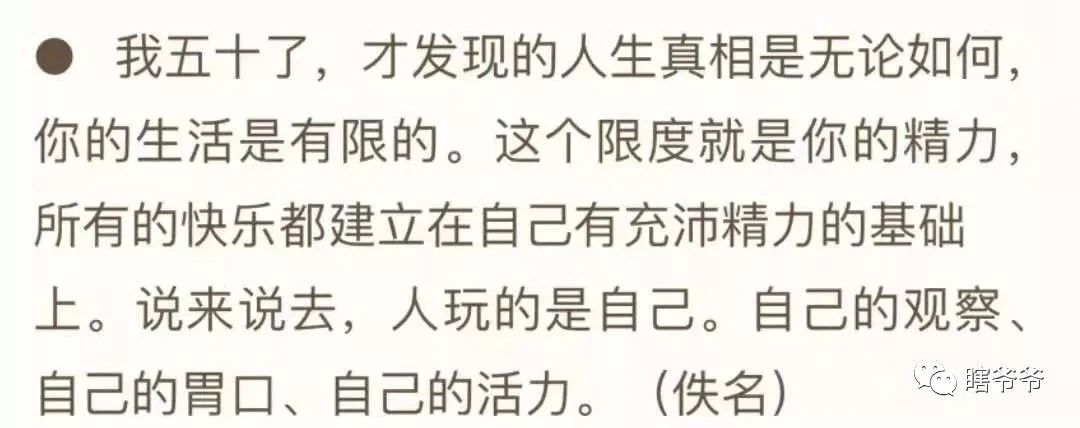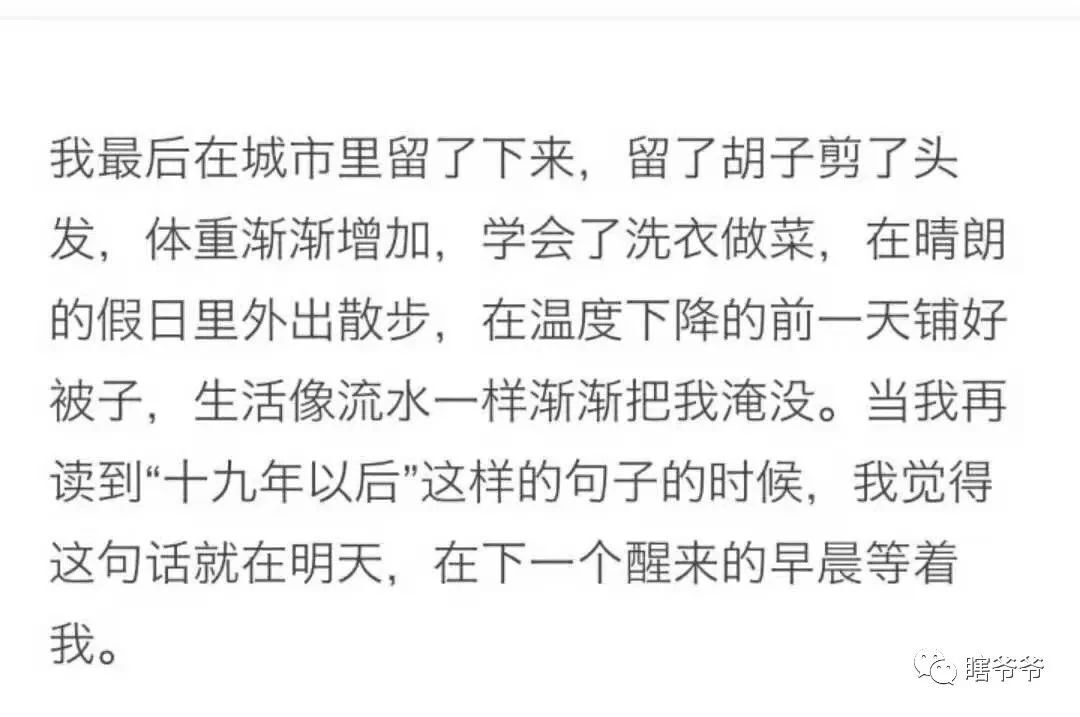2021年的第三日,早上去公园遛狗,准备过马路,一个广东靓仔,骑着小黄车,他的女友,站在自行车后面,没有坐在宝马里哭。
一位老妇人,骑车迎面过来。
头顶上,一轮皓月当空。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我想起来昨天晚上临睡前看前几天去世的作家黄孝阳的作品《人间值得》。
然后我在心里问自己:人间值得吗?
值得!我听见自己心里的回答。
01
我出生的时候,是腊月初二。天寒地冻,我母亲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日子。
我出生的这个家庭,我奶奶,我父亲,我母亲,我小姑。我是这个家庭的第五个成员。
我爷爷去世的早,我奶奶努力拉扯大了四个孩子。我大伯父没有结婚,生病不得医治自缢而死。我大姑已经出嫁。
我父亲当时应该是24岁。我母亲比他小两岁,22岁。
我出生的那天早上,有一队串联的红卫兵从我们家后面的公路上经过。来我家叫我父亲出工的生产队长猫眼,他的外号叫猫眼,他说,这个孩子就叫串联吧。然后我就有了这样一个奇怪的乳名。
我们当地有一种奇怪的说法,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从外面来的第一个人,是来踩岁的。岁,在这里读设。他们认为,刚刚出生的这个小孩,会和这个踩岁的人有着某种奇怪的联系。
我后来读圣经,看到耶稣出生的时候,有所谓的西方还是东方三圣人来送礼,还有读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郭靖出生的时候,所谓的江南七侠的出现,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意味深长的相遇。
我后来和这位被我按乡邻习俗叫做二大爷的猫眼队长并没有什么交集。
倒是我偶尔回乡的时候,在村口街头看到他,称呼他一生二大爷,他会问,你是谁?我是说我是谁谁谁啊,那个谁的儿子。他就恍然大悟:哦,你回来了,小唻。回来看你娘啊。
小,是长辈对自己晚辈男性的称呼。
我的故乡在老去,他也在老去。
02
出生第三天,我病了,发高烧,烧得脸通红,发紫。我奶奶把村里的神婆叫来,神婆看看,说,这个孩子没救了,准备送狼食岗子吧。
我奶奶,这个身材高大、强悍、善良,有时候有蛮不讲理的的北方老太太,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完了,起来,去邻居家挨家挨户借钱,借了五块钱,送我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说,再晚一点,这个孩子没命了。
年二十七,我出院,全家人回到家。家里没吃没喝,我奶奶把堂屋里起隔离作用的篱笆帐子拆了,烤火取暖。
那个时候,是真穷。
上面这些所有的故事,都是我奶奶,或者我母亲回忆起来,告诉我的。
我是我奶奶的长孙,这个守寡的老妇人,在养育大了自己的四个子女后,开始承担祖母的责任,为她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儿子,养育孩子。
我从小跟着我奶奶睡。晚上吸吮着奶奶干瘪的乳房睡觉。她像老母鸡护持自己的小鸡仔一样,把我养大。
所以,小时候,我很胆小,很内向。因为一切都有我奶奶。出了任何问题,我只要躲在我奶奶身后就可以了。
而我的母亲,在我奶奶眼里,是个吃才无用的废物。她看不起我母亲,相信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婆婆大骂儿媳是应该的。以至于时至今日,我母亲回忆起我奶奶来,都心有余悸,说:你奶奶,对我,那是真狠。
03
我爷爷弟兄五个,他是老五,最小。所以兄弟几个分家,他得了祖屋,还有一些家私。我的没见过面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显然是最疼爱他最小的儿子。
但还是架不住家穷。我奶奶告诉我,她要过饭,要饭到过黄河北。
我们家的祖屋,三间堂屋,一两间西厢屋,有大门,甚至还有简陋的门楼。到了后来,我父亲还把这个院子翻盖了一遍。
院子里有香台子,上面是拜神放香供神的地方。下面是鸡窝。有猪圈,甚至有粪坑,积肥用。有一棵枣树。还有几棵高大的槐树,家槐。
家槐树上有喜鹊做窝,还有乌鸦。春天的时候,槐树的嫩芽爆出来,明黄色的嫩芽,摘下来,可以炒着吃。然后槐芽老了,变成槐树叶,开花,黄色的花,可以摘下来,晒干,卖到供销社,说是可以做染料,解放军穿的黄军衣,就是这个染的。
槐树上还有一种神奇的中药,叫槐黄,是树感染了真菌长出来的一种东西,我奶奶看下来,谁如果摔伤了,用个煮鸡蛋吃,会好得快。功效和牛宝类似。
然后槐花老了,结出槐连豆子。乌鸦和喜鹊吃了,落在地上,会长出小槐树苗来。如果移栽好了,真的可以长成大树。
我们把乌鸦叫老鸹,老鸹窝一般在比较高的树杈上,我小时候调皮,曾经上去过,看见老鸹窝有刚孵出来的幼鸟。有小玻璃珠,有鹅卵石。
鹅卵石是从我们村子北面的河滩上叼来的。乌鸦喜欢闪亮的小石子。我们叫老鸹枕头。因为大人告诉我们,老鸹睡觉的时候,就把鹅卵石当枕头。
夏夜,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没有电灯,连油灯也点不起,漫天的星星,我奶奶指着天上的银河,说这边的是牛郎星,那边的织女星。银河是王母娘娘的银簪子画出来的,目的是隔开牛郎织女。有流星划过夜空,我奶奶就说,那是地上又少了一个人。
她还说,七月七的时候,躲在葡萄架下,能听见牛郎和织女说话。
这个时候,如果有夜猫从墙上走过,和什么动物打架,我就会吓得躲进奶奶的怀里,然后睡着了,我奶奶就会把我抱进屋里,放在床上。
这就是我的童年。
04
我们家的房子算是在村子的最北面,后面是菜园子。那个时候,水位浅,菜园子要浇地,用辘轳把水打上来,然后倒进水渠里,让水流进菜地里。
菜,主要是白菜、菠菜、芹菜、青椒、黄瓜、茄子、韭菜。还有土豆,我们家叫地蛋。
我父亲还会种山药。种山药要挖很深的沟。还有专门的铁锨。山药会结出山药蛋。
再后来,生产队还种西红柿,我们叫洋柿子。我记得我和小伙伴从玉米地里钻进生产队的洋柿子地,趴在地上,专捡熟透的吃,吃的肚子滚圆,再爬出去。那个时候,少用化肥,也不打农药。
菜园子北面,是我们家祖坟。有高大的坟头,长满了茂密的坟草。还有几棵高大的白杨树。
大人一般不让孩子去,说那个地方紧。紧的意思是鬼神之地,会闹鬼,小孩子会受惊吓。
........
05
突然发现,我只是想着试图回忆一下童年,然后好迅速转入我的成长,我的漂泊,但我发现,要想把我想说的说清楚,需要很大很大的体量和工程。
我只能在今天,因为篇幅的关系,把这种回忆暂时打住。
回到开头黄孝阳的《人间值得》。他在这本书的创作谈里这样写到:
《人间值得》这个书名二十年前就在脑子里盘桓。与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人事有关。
一个是在县影剧院卖票的年轻人,长得很帅,据说以权谋私与几位异性同时保持了不正当关系,以流氓罪被枪毙了。同牢犯问他后不后悔,他说值得。
一个是邻居大哥,人品有问题,打小即听闻他各种偷鸡摸狗、作奸犯科的事。人长得也瘦小猥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去广东,路上出了车祸。本来是有机会活下来的,可他偏偏不肯老老实实躺进救护车,翻进爬出,从倒覆的车厢内背出十几位伤者,还直说自己没事。第二天人就倒下了。说是内出血,如果当天能上手术台就好了。据说他的遗言就是“值得”两字。
还有一个就是同学嘴里的某某某。那时县医院门口有几个贼,专门偷乡下赶来看病的人。他撞见了,开口叫破,还死命拽着那贼的手让他还钱,结果被贼的同伙打得脑震荡住院。好多人说他蠢,我不这样觉得。他大我几岁,是我的朋友,尚还没有把我打得头破血流。我偷了一本《鹿鼎记》去看他。我们在秋日的暖阳里拼命地背诵金庸小说的章节回目,互相PK,当他念到“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时,突然甩袖轻叹,吐出四字,“人间值得”。
同学某某某死了。小说的主人公张三也死了。但还有百个千个万个的“他们”还活着,他们不是乡村秩序下的蛋,也不是都市文明的孩子,他们体内的基因片断是在一个被现代性浪潮重组的过程中,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紧密勾连,有诸多崩毁残存,亦有突变进化。他们人至中年,现已多半在事实上成为县域政治经济文化各生态系统内的话事人,是权力的毛细血管,亦是各种潜规则与隐秘秩序的制定者,谙熟不同的话语体系,自如切换,能在一个时辰内分别扮演畜类与人类。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尚未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的主体部分,在实际日常层面开始影响大多数百姓的生活。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城,这是一个极广袤的如同风暴一般的现实,是“真实的真实”。
而他们中的一小撮人,比如张三,试图从历史与现实情境等维度,以及生命意志的高度,反思“人”这种奇妙存在,讲述唯独属于他们的故事,或者说传奇,故而《人间值得》。
读完他的这段文字,我就在想,我的乡村生活,我的县城生活,我的北上广深的漂泊,难道仅仅是我个人的生活吗?它们不是构成了中国最近40几年的生活图景吗?
如果我按照我生命的履历写出来,乡村生活、县城生活,北上广深生活,它们应该既是我的个人史,也是时代史,国家史。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遗失的灵魂》里说:“如果有人能从高处俯瞰我们,他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汗流浃背的、疲惫不堪的人流,以及他们姗姗来迟、不翼而飞的灵魂。”
卡夫卡说过:“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
我是那个穿过了暴风雨的人,也是下面这段截图文字里的人:
06
下面,请容许我抄录一段文字:
我记得有一天在旅行途中,我从列车车窗向外张望,我努力想从我面前闪过的景物中撷取一些印象。我是一边看,一边记下眼前一晃而过的农村小墓园,我记下树丛中阳光照射下一条条光束,还有像《幽谷百合》中描述的路旁种种花草。以后我又反复回想那照着一条条阳光的树木,乡村的小墓园,我反复追想那样的一天,我试图真正领会那一天自身,而不是它冷冷的亡魂。但是始终做不到,没有成功的希望,我绝望了。可是有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我的汤匙无意中落在磁盘上,调羹在磁盘上发出的声音,正好和那天列车靠站扳道工用铁锤敲击列车车轮的声音一样。就在这一分钟,声音敲醒的那个难得一遇而又不可理喻的时刻,又在我心上复活,这一天,完完整整地在其全部诗意中又在我心中活了起来,只是那村中墓园,布满一条条阳光的树木何巴尔扎克式的路边野花却排除在外,因为这一切是经过有意识的观察取得的,诗意的再现全部丧失了。
这样的对象,我们是会不时一遇的,那已经失去的感受,也会使我们为之心动,但是,由于时间相去太远,那种感受我们已经不可能指明,不知称它什么才好,所以也就不复再现,真可叹惜!又有一次,我走过一间配膳室,玻璃窗一处打碎的玻璃上有一块绿色的布片堵在那里,引起我的注意,我立即停下来,心中若有所动。一道夏日阳光这时正照射在我的身上。是怎么一回事?我试着去回想。我看见有几只胡蜂在阳光下飞动,桌上樱桃散发出香气,我已经不能再回忆起什么了。——时间,我就像夜里睡着的人醒来不知身在何处那样,只想分辨身体是在哪里,以便知道这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时睡着的人并不知道是睡在哪一张床上,在怎样的房间里,在什么地方,是他一生中的哪一个年份。一时间,我就像这样,处在恍惚犹豫之中,试着在那挂着一块绿色布片的周围摸索着,设法在我惺忪初醒的记忆中把时间与地点加以定位。这时,我始终是处在生活已知或已忘却的感觉的一团混乱中迟疑不决,无所适从;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过是一刹那之间。随后,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记忆又复陷于沉睡。
我的一些朋友在散步中不知有多少次看到我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看到我走在我们面前的一条小径前停下脚步站着不动,或者是在一丛树木前面又驻足不前,我要求他们让我一个人留下,在这里停一停!就是这样,也是徒然;为继续追索那已过去的时间,尽管我闭上两眼一再努力也无济于事,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随后我又突然睁开眼睛,像第一次看到那样着力再把那些树木看上一看,究竟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这些树木,我仍然盲然无所知。我认识这些树木的外形,这些树木的姿态布局,它们呈现出来的线条,就仿佛刻在某一幅令人心爱的神秘的画幅上,直在我心上颤动。但是,对此,我什么也说不出,而它们却像是由于自身天然而多情的意态姿影不能得到表现、不能告诉我它们觉察我不能辩明的那个秘密,倾诉着它们的懊恼憾恨。一段亲切的时间的幻影,是这样亲切,以致我们竟为之心跳,跳得心都要碎裂开来了,它们就像埃涅阿斯在地狱中遇到的鬼魂那样,向我们伸出软弱无力的双臂。难道这就是我在幸福的童年时期经常去散步的城郊?难道我以后只能在想象的国土上梦见妈妈,那时她病得那样厉害,在湖水之滨,在那夜间也是明亮的树林中,这的确是梦中的土地,真实得几乎和我度过童年生活的地方一样,难道这仅仅是一个梦?对一切我竟茫茫然一无所知。我不得不赶快追上我的朋友,他们在大路拐弯处正等着我,我怀着焦急的心情,对着一个过去的时间转身走开,这过去的时间从此我是再也见不到了,向我伸出无力又多情的手臂的逝去的一切,从此也只有弃置不顾,可是,那逝去的一切似乎正在向我说:让我们再活转来。在我还没有回到我的同伴的身边,和他们谈话之前,我回身再看一看那无声而富于表情、渐渐逝去、依然在我眼前萦绕不已的树木曲线,我投去的目光也渐渐模糊,越来越看不清了。
与这样的过去、我们内心最熟悉的精髓相比,智力所提供的真相似乎并不真实。因此,当我们投向那可能帮助我们重新找到那已成过去的时间而又力不从心,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被这类才智之士所理解也是势所必然的,他们不明白艺术家是独立的一个人,他们不理解艺术家所看到的事物的绝对价值并不仅仅对他才有重要意义,他们也不知道这种价值的量度只能在他身上才能找到。艺术家可能在外省一家剧院上演一场可憎的音乐演奏会,演出一场让有艺术修养的人认为是可笑的舞会场面,这样的舞会甚至可能比歌剧院精彩演出、圣日耳曼郊区最漂亮的晚会更能引起他的一些回忆,甚至在他那里可能提高到一种凝神沉思的境界。对火车时刻表上的站名,艺术家也喜欢借以想象。一个木叶飘落、寒气袭人的秋夜里,一本平庸的书,对有艺术修养的人也充满着他从未听到过的一些人名姓氏,对他可能有一种哲学名著也无法比拟的价值,这可能让有趣味修养的人士说:一个有才能的人竟然也会有这种愚蠢的兴趣。
对于智力如此不加重视,我竟以此为题写了许多文章,接下去我还要一反我们听到、读到的庸俗思想继续写智力所提示的这些想法,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我把我许多小时候都算在一个小时之内,(其实,所有的人不都是这样吗?)以此写一部出于“智力”的作品,也许不免轻率。不过,出于智力的真理即使不如前面所说感受力的秘密那么值得重视,但也是其值得重视的方面。一位作家只能是一位诗人。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在我们这个并不完善的世界,以及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艺术杰作,也不过是伟大才智遇难沉船飘散在水上的一些残留物,即使是这样,将散见于外的情感之珍宝借助智力的网络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仍然是他们。如果人们相信,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人们没有认识到他的时间中那些最为美好的时刻,那么,破处怠惰迟钝,感到有必要说出他亲历的时间,这样的时刻必将到来。也许圣伯夫的方法并不是处在第一位的主要对象。不过,人们在阅读以下篇章的过程中,也许会被招引注意看一看圣伯夫的方法所涉及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有关智力的问题,我在开始谈到智力所处这种低下层次的性质,对于艺术家来说,也许是最为重大的问题。而智力这种低下层次的地位,依然需要智力给以确立。因为,如果说智力不配享有高尚的王冠的话,那么,也只有智力才能颁布这样的命令。如果智力在效能的等级层次上居于次要地位,那么,也只有智力能够宣告本能处在首要地位。 ——马塞尔·普鲁斯特《驳圣伯夫》 王道乾/译
07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谅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做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王朔《动物凶猛》
多年以后,我也离开了小镇,每一次回去,都会有一些人再也无法见到。每一次在路途中见到那些荒凉、简陋、破败的小镇时,我的心便格外柔软、疼痛,我都会想起我那个不起眼的,被人遗忘的,让人心碎的灰暗小镇,想到那些如麻风病人的脸一般糜烂的墙壁,想到那些结着蜘蛛网的像瞎眼老人一般空洞的窗户,想到平原上的熏风,刮过小镇时,那些颤抖的瓦片……正如赫塔·米勒所说:只有在这死亡遍布的地方,才会让我感觉到些许的温暖。” 盛慧《外婆家》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 1975 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卡勒德胡塞尼《追风筝的人》
08
归途漫漫,人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