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飞剑客

笔者记得,刚开播的时候豆瓣评分上了8.6,大抵是因为开篇场面宏大,服化道做得还不错,后来风评一路下滑,沦为了大情妇,槽点慢慢多了起来,诸如前期宫斗戏太多了,张鲁一不适合演嬴政,还演的是13岁的嬴政,叫一声母亲,令观众的背脊发凉,就应该和吕不韦去浪迹天涯等等。
帝王戏怎么拍好,笔者想孔鲤同志那篇《秦国为何要统一?帝王戏为何难拍好?》已经很好指出了,在此不赘述。作为大秦帝国最后一部,根据剧透我们也应该明白,六国终将统一,所有角色都是“天下统一”的意志的机械容器,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将统一进行下去,我们是愿意看下去的,但编剧如果想把大秦塑造为万民向往的好国家,秦君爱民如子,引得楚人不愿意做楚民,想做秦人,这就不好,这会伤害大泽乡男儿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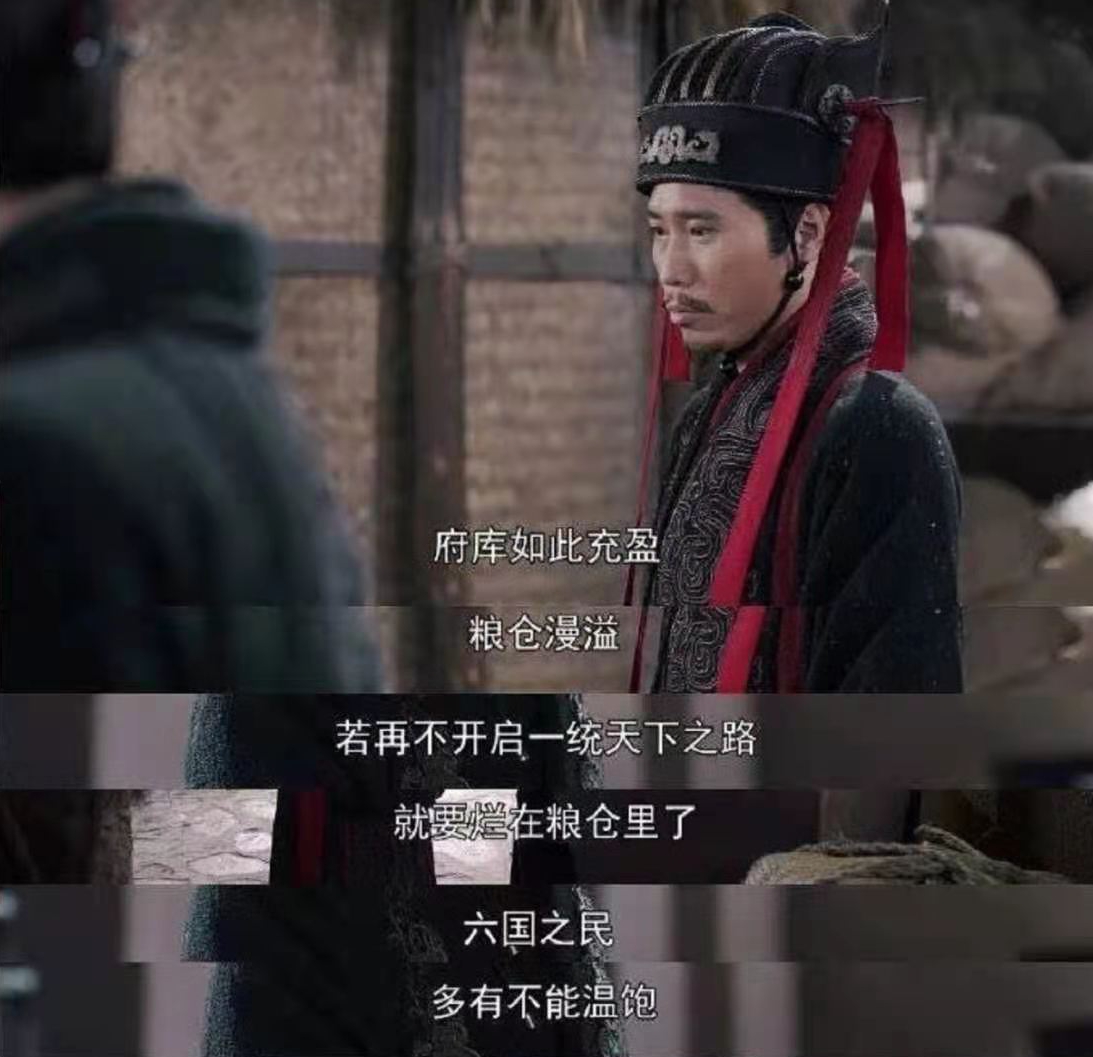
坦率说,剧的很多问题,要追溯到孙皓晖的原著《大秦帝国》,小说本身是秦人看秦国,类似当今陕西人回忆祖上如何筚路蓝缕,如何阔过,写得爽是爽,就是稍微不太尊重关东各国,比如六国女人,都会深深被秦人所折服,不顾一切爱上他们,因为六国男人费拉不堪。作者从第一部开始就喜欢强调老秦人的精神,但事实上,秦国能一路走来,客观上的战争机器设计,才是主因。
孙皓晖写的是历史吗?当然不全是,先不说对儒家和六国有什么偏见,几对君臣关系也有相当多的美化,跟历史上实际形象有些距离,战国时代毕竟跟后世推崇的“明君贤臣”那一套不同,除此之外,他的笔下的秦国君臣带有强烈的基层干部色彩,老秦人不像是2000年前的黔首,像工厂里的标兵。其实在看第一部电视剧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秦国君臣换个皮说是我党干部,也像那么回事,同时我记得有这么一段,秦孝公在那跟太后讲政策,咱们老秦人一大家子住在一块,别的地方的人一看,不愿意来……你看,这简直就一带领乡亲们移风易俗招商引资的老支书。
那《大秦帝国》是小说吗?也不尽然,虽然采用了小说的体制,但其写作技巧上干瘪单调,除了第一部的商鞅,以及最后面的嬴政,人物都像是走马灯式的上场、谢幕,更像是自己的人偶和传声筒。小说情节中还大量夹杂着政论、历史考据,兵器车马绘图等等,如果人物不足以传声,作者还会像太史公一样随时跳出来评价,完全不在乎小说形式,不在乎人物塑造,有没有文学性。根据刘复生老师的说法,作者应该是把自己当希罗多德了,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诸如希罗多德和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他们的写作是要追求失落的历史真实?非也,是为了现世训诫。
一个政法教授絮絮叨叨写了十几卷,写火了十几年,还衍生出了四部剧,甚至被做成了各种“大秦”公司管理学、商战攻略、成功学,这些都不是他的本意,关键在于要借帝国回应什么?
如同笔者在《刘慈欣:一个冷战的幽灵》写道:
(刘慈欣)年轻时代身处冷战夹缝中的第三世界中国,一个知识分子从政治运动和高积累中走出来,就像罗辑从冬眠中复苏,人类从大低谷走出来,努力发展民生科技,是“科学的春天”,也是“卖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以“以市场换技术”的时期,是中国科技预算削减,武器和战略工程的“飞地”难以为继、逐步瓦解的时期,这个时期空气中仿佛依然飘浮这智子。
而到了九十年代,据说历史已经终结,末人们开始狂欢,他们绝不感谢手握两个文明的按钮以此换来和平发展的执剑人罗辑,而是选出程心这样的白左;也就是在九十年代,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优秀人才被经济学家和哗众取宠让世界充满爱的公知取代……
作为一部同《三体》差不多时期,诞生于冷战结束,全球化深入又逐渐走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好似愈演愈烈的世界里,《大秦帝国》自然是不止于写秦国,还要你去代入老秦,让你热血沸腾。他想要在这样的时代去解决中华文明是什么,何处来的问题?从这方面去思考,《大秦帝国》里无疑充满着现代中国的起源的历史隐喻。譬如,大秦帝国的起点于少梁之战,秦献公中箭重伤而死,强魏压境,东方诸国虎视眈眈,新继位的秦孝公被迫屈辱求和,哪里来的百年国恨?哪里来的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无非是我们经历过。
先声明:接下来谈的不是秦国历史,而是对应小说的原初的意义上创立国家的故事。
这是一个现代话题。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这句话分享着这一种共同命运感,在列国世界里,这句话是激励无数将士朝臣慷慨赴死的源泉,是每一个秦人无法拒绝的使命召唤,因为国难,一个经典意义的利维坦诞生了,对内它结束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同时它亟需立法者,于是有了商鞅变法,变法标志着帝国的正式出现;然而共同体有着不能约化的小共同体,于是有了儒法之争,有了《吕氏春秋》的妥协,小说里处理成了秦王政与吕不韦的政治理念上的冲突;随着可动员人口急剧增多,君主要维持各阶层的稳定和平衡,势必要走向扩张;扩张是利维坦将共同体扩大化的脚步,从而结束了“天下”的自然状态。是为统一。
这里概述一下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自然造就的人类族群内每个个体的力量对等,出于竞争和猜疑链,人们就可能会在没有共同权力的约束下陷入人人为敌、他人即是地狱的战争状态(有点黑暗森林那味)。由于对自然状态的混乱的恐惧,人们共同订立契约,约定各自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托付给某一君主或者政府,形成一个足以令每个人都因恐惧而效力的权威,即利维坦。自此,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对于横死于他人的恐惧消失,转化为对于利维坦的恐惧,正由于存在了国家这样一个共同权力,人们相互之间也终于可以产生法律关系,才得以立法,一旦有人背叛约定,等待他的将是利维坦的制裁。
“天下”的自然状态结束以后是什么景象呢?
是百代皆行秦政法。
也就是说,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不是从暴力(秦法)中创立的,后来的王朝都需要假借秦的暴力来完成,并且假借着秦的暴力在维持着统治。
在《大秦帝国》里对我们国家和文明的溯源里,孙皓晖似乎笃定了法制才是立国的根基,但在他对于法家的过度美化塑造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这种法制思想与其说来自两千年的大秦,不如说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对现代国家的追求,其中明显的是对儒家的彻底批判,这是五四一直到八十年代的主旋律,也比较贴合孙本人的人生轨迹。
成长于新中国探索时期、深受儒法斗争话语熏陶的法学教授,对儒家自然没什么好感,不仅如此,还捏造了张仪怒斥腐儒孟子,孟亚圣辩不过就吐血三尺等桥段,以此疯狂嘲讽儒家。但教授似乎忘记了他笔下极端排斥儒家和六国浮华的百家的大秦,在历史上二世亡国,以至于后世儒学家们一边坐在大秦的坟头诵读没烧掉的经书(蹦迪),一边咒骂,暴秦(傻X)!
当然,对暴秦和秦始皇的有意见的不仅仅是儒学家,五四以来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左派知识分子都在咒骂暴秦,毕竟焚书坑儒能让知识分子共情,劳动人民不堪忍受苛政也是事实,还有人会借秦始皇劝诫或映射当局,比如郭沫若就经常借历史剧中秦始皇映影射委员长,建国后他还专门写了对秦王政的批判,毛教员看了这些批判以后,一言难尽,还是对郭老说:
劝君少骂秦始皇……
教员无疑是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的,同时只有他明白新中国创制的艰辛,为此在后期还发动了评法批儒,这或多或少影响到了《大秦帝国》的作者以及诸位读者。实际上,原初儒家的反动性起源于小的宗法共同体,这是铁器时代的生产力怎么也无法消灭的,反而助其生长,即使到了大一统深入人心的时代,皇权和法家依然无法下县,封建统治者必须得依靠儒家进行地方治理,依靠基层的宗族进行治理,在明清以前的中央,也有相权制衡,这都是儒法共治。皇权时代的儒法尚能沆瀣一气,当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时,陷入内乱割据,重复战国时代,一统后重新分配(赃)。
然而我们的近现代史却有着刻不容缓的事情。
《大秦帝国》要批倒所谓儒学——我们的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任务亦是如此。当然,这个“儒学”可不仅仅是孔子创立的思想体系,可不仅仅是孔家店,还象征着各种小共同体的阻碍:基层宗族,地方割据、豪强,民族分裂势力,面对民族危亡的外部危机,我们要建立一个巨型利维坦,就是要不断打破各种小共同体,打破一盘散沙的局面,整合中国人,确立统一的国家认同,这是五四启蒙运动以来的努力,包括北伐打倒军阀,抗日,解放全中国,我们仿佛能看到《大秦帝国》中秦的使命,就是近现代中国创制的努力。
这个民族国家的使命最终被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不仅驱除了列强,结束了内战,扫清了割据势力,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完成了对基层社会的动员和改造。
但这未必能是一劳永逸的,这个时候,我们或许会理解教员对郭老的奉劝的良苦用心,少骂秦始皇,前提是多读柳子厚、王夫之们,不是说不反苛政,事实上大泽乡的陈胜吴广就是大秦苛政的否定面。而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来说,虽然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但对外帝国主义势力还没有灭亡,对内的宗法的、割据的、分裂的毒素还没有清理干净,随时会反扑。
这里要说到秦始皇及其形象,无疑,主席是不想多做否定的。但到了八十年代地方分权以及新启蒙的文艺思潮里,秦始皇就重新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的靶子。尤其是电影这边,第五代导演好像都对秦的故事,尤其是刺杀秦始皇的故事的情有独钟,陈凯歌拍了《荆轲刺秦王》,把秦始皇塑造成一个善变、歇斯底里、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统治者,这时候大战秦俑里的张艺谋把自己包上泥烧成了兵马俑,这些都是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叙事。
多年以后,事业有成的中老年张艺谋拍了《英雄》,表示愿意为了天下舍弃成全嬴政,不知是否想起年轻时的他敢为情背叛秦始皇,敢当儒生抗拒大一统?这都无所谓了。这里是说张艺谋们理解了教员的话?不对,更可能是张导们成为了既得利益者,讨厌的人已经不在。所以戴锦华说张艺谋拍《英雄》是在给后革命时代的革命驱魂,给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加冕。
和这些文艺老油子借古喻今比起来,《大秦帝国》又在关注什么现实问题呢?
就像我的老师刘复生所著述的,诸如《大秦帝国》、《三体》,他们的背后都有政治思考和政治的无意识,他们都诞生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深入又逐渐走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好似愈演愈烈的世界里(或者说霍布斯式的黑暗从林里),强势文明的霸凌,边缘文明和国家人民的惨状(伊拉克、叙利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兴起和破坏,都充斥着日常媒体,带来了对外来文明的恐惧,提示着我们利维坦的重要性,这个时候,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中产阶级,都会寄希望于国家保卫自己的利益,于是乎,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渐占据主流。
除了外部的威胁,我们也面临从八十年代以来的国外买办及其自由主义,中部豪强,宗族势力的死灰复燃的局面,面对这些阻碍,国家主义能否整合共识,同时不陷入儒法之争的窠臼中?但正如目前我们看到的,在这套意识形态里,诸如效率与公平,入关人大战分配人等,依然充满着类似儒法之争的裂隙,由此我们也需要追问,国家主义是不是我们的终点?
不妨看看天安门城楼上的两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