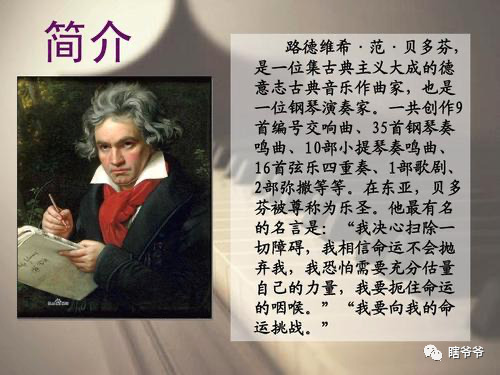01
今天是12月22日,2020年的最后倒数第十天。10天之后,是2021年。
按理说,我应该在2021年前面加个定语,崭新的,问题是,它是崭新的吗?
下面是NEW YORKER 2020最后一期的封面:
2020年最后一期New Yorker封面,精准传神。仔细看每个细节:
蝙蝠,将Clorox消毒水当酒喝,妈妈在家监督孩子的zoom class,孩子衣服上一个大写的Q(QAnon),濒死老人在倒计时,某人在销毁自己的tax return,其实是在给疫情煽风点火。还有二楼那个越抹越黑的。
这个封面几乎总结了2020年的美国全貌。
很多面孔,川普,朱利安尼,库什纳,......
那个推门进来的孩子,名字叫2021。他戴着口罩。
令人想起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结尾:
圣者约翰克里斯朵夫终于渡过了河。他肩上扛着一个沉重的孩子。他放下孩子,叹口气说: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那孩子回答。
刚刚看新闻,说索尼耳机用贝多芬做营销的事情上了新闻热搜。
12月16日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纪念日。索尼用这一天做梗,看来是良苦用心。但他们却忘记了,贝多芬是个聋子。
26岁的时候,贝多芬就发现了自己的耳疾,但这个时候,这个伟大的音乐家已经写出了《悲怆》、《月光》。所以,他拼命掩饰自己的耳疾。
因为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耳朵聋了,意味着自己艺术生命的结束。
所以,他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向命运挑战。
他成功了。
30岁的时候,他彻底聋了。但他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几乎都是在他30岁耳聋之后完成的。
所以,罗曼罗兰在他的三巨人传之《贝多芬传》里这样写到:
30岁,对有的人来说,才刚刚开始,对有的人来说,他已经死了。
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30岁的行尸走肉。
03
昨天晚上,临睡前看微博,@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 写了一篇关于朱军案的文字,是为朱军翻案的文字,意思是朱军是冤枉的。
作为吃瓜群众,我们不是当事人,不知道真相,只能按照自己得来的信息和理解做自己的判断。
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朱军的那么多好朋友,很少见到为他发声的?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有点不可理解。
这篇文章提出的一点,我有点赞同,就是告朱军的弦子,还有弦子的那个朋友的面相:
坦率地讲,我第一次看见弦子的照片,我莫名想起来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04
读过中学的学生,都知道历史课本里的杜甫画像:
其实,历史上是没有杜甫的任何画像,更不用说照片了。
1952年,周恩来总理收到莫斯科大学来函,希望中方提供素材,以完成大礼堂的世界各国科学家拼贴像。
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认为,李时珍和祖冲之最为合适,但遍寻汇集古人画像的南薰殿和《三才图会》,都没有找到这两位科学家的画像。
周恩来总理指示,“画历史人物,找蒋兆和。”
于是,这个任务落到蒋兆和身上。蒋兆和(1904-1986)出生在四川泸州,是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当时,蒋兆和的人物画艺术造诣已经很高。
李时珍从来没有过画像,样貌只有《本草纲目》序言里的一句——予窥其人,晬然貌也,癯然身也。
这个形容让蒋兆和想到了萧龙友先生。
萧龙友是蒋兆和的老丈人,也是当时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跟李时珍的身份也算对应,于是,蒋兆和照着萧龙友的样子,画出了这副李时珍的画像。
萧龙友与《李时珍像》
画祖冲之的时候,蒋兆和的蓝本则是科学家竺可桢。这之后,蒋兆和又如法炮制画了刘徽、张衡、张仲景、僧一行、孙思邈、郭守敬等古代人物的画像。
竺可桢与《祖冲之像》
蒋兆和作古人像
这一系列古人像中,《杜甫像》是最深入人心的,这幅画是蒋兆和1959年创作的,被纳入高中语文课本,近几年更是因为各种版本的“杜甫很忙”在网上风靡。
这次杜甫画像的原型是蒋兆和本人,在画的右边,他提款道: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千载岂知逢新世,万民欢唱大同时。我与少陵情殊异,提笔如何画愁眉。”
05
都知道,在中国,奸夫淫妇的代表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可以说,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西门庆和潘金莲。
那如果为西门庆和潘金莲画像,他应该长什么样?
港台大陆拍了很多影视剧,关于金瓶梅、水浒传、潘金莲、西门庆,对于西门庆,大多是突出他的“潘驴邓小闲”。
最近热播的《大秦赋》,里面的嫪毐,更是引起了人们的讨论。有人觉得遗憾,看不到他的巨大的那个,有人嫌他占的戏份太多。
回到西门庆,你觉得,西门庆应该像谁?
06
我以前说过挂相。
什么叫挂相?女作家毕淑敏曾经这样谈论过女人的挂相:
对一个女性最有害的东西,就是怨恨和内疚。前者让我们把恶毒的能量对准他人;后者则是掉转枪口,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对准了自身。
我有一个面目清秀的女友,多年没见,再相见时,吓了我一跳。
一时间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她倒很平静,说:“我变老了,是吧?”
我嗫嚅着说:“我也老了。咱们都老了,岁月不饶人嘛!”
她苦笑了一下说:“我不仅是变老了,更重要的是变丑了。对吧?”
在这样犀利洞见的女子面前,你无法掩饰。
我说:“好像也不是丑,只是你和原来不一样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面目都不同了。”
她说:“你不知道我的婚姻很不幸吗?我说,知道一点。”
她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一个不幸福的女人是挂相的。
我们常常说,某女人一脸苦相。其实,你到小姑娘那里看看,并没有多少女孩子就是这种相貌的。
女子年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天真烂漫的。但是你去看中年妇女,就能看出幸福和不幸福两大阵营。”
我说:“生活是可以雕塑一个人的相貌的,这我知道。但是,好像也没有你说得这样绝对吧?”
她坚持道:
是这样的,不信你以后多留意。
到了老年妇女那里,差异就更大了。基本上就分为两类:一种是慈祥的,一种是狞恶的。我就是属于狞恶的那一种。
我不知如何接下茬,避重就轻说:“不过,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老年人,都是慈祥的。”
她说:“对啊。那些不慈祥的,根本活不了太久。比如我,很可能早早就告别人世。”
话说到这份上,我只好不再躲避。
我说:“那么你怎样看待自己的相貌变化?”
她说:
我之所以同你讲得这样肯定,就是从我自己身上得出的结论。
因为我的婚姻不幸福,我又没有办法离婚,所以一直在怨恨和后悔中生活、煎熬着。对着镜子,我一天天地发现自己变得尖刻和狞厉起来。
当然,这不是一天发生的,别人看不出来,但我自己能够看出来。我用从自己身上得到的经验去看别人,竟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我看着她,说不出话来。在这样透彻冷静的智慧面前,你只能沉默。每当我想起她来,心中都漾过竹签扎进甲床般的痛。
她所具有的智慧,是一种波光诡谲入木三分的聪明,犹如冰河中的一缕红绳,鲜艳地冻结在那里,却无法捆绑住任何东西。
这是我看到的对女人挂相的最感性的一段描述和分析。
可参看《为什么有些中年男人特别令人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