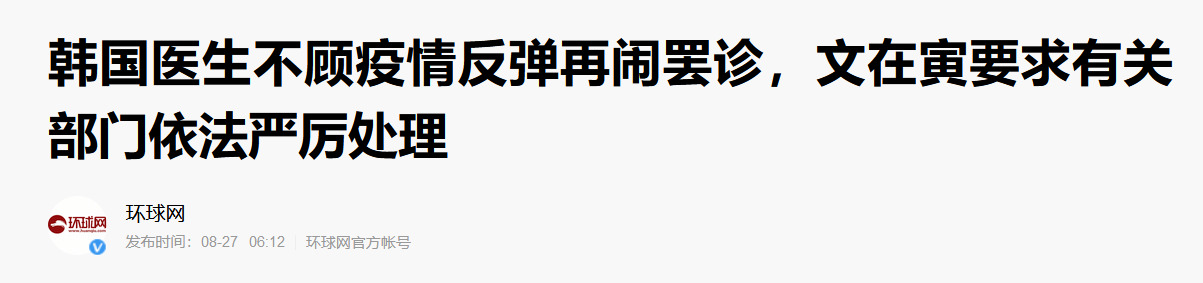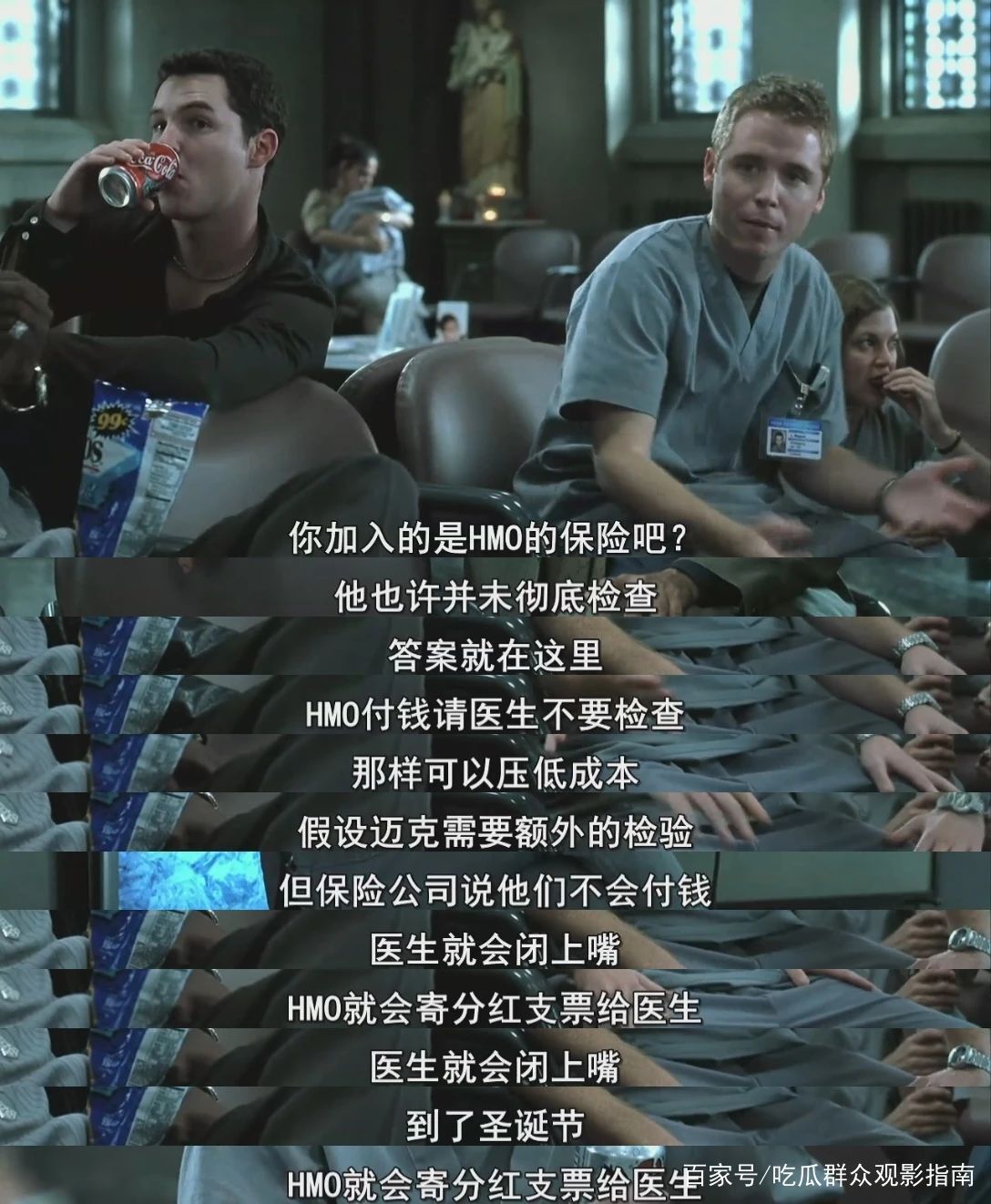近日,韩国医生集体进行抗议活动,表达对于韩国进行的医疗改革的不满,由此韩国的医疗系统出现了各种问题;而与此同时,韩国的疫情陷入了第二波爆发,18天内有5177例确诊,防疫再次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时间,显然是有点尴尬的。但是更加尴尬的是,韩国医生不满的原因。
工作压力大,待遇不足,医患关系僵硬的问题,是全球医务工作者都在抱怨的,哪怕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生,抱怨的主要问题都是这些。但是韩国医生的不满并不是如此,他们不满的原因是韩国扩大了医学院招募规模。说的更直白一点,他们担心扩大医学院招募规模影响目前这些医生的待遇。
按照新闻报道的说法,韩国方面打算在十年之内,扩招四千名医学生,平均每年四百人,这个数量相比韩国的医护人员总数,其实并不算非常多。单是参与这次活动的韩国医生,就有十三万人。扩招四千人这样一点的数量,放在十年的时间,就算落实了,对于实际上的待遇影响恐怕并不大。这样的活动更多的是表达一个姿态,他们不能允许自己的蛋糕被别人摆弄。
只是,现实的情况是,这个数量就算落实了,对于韩国目前需要面临的挑战,也是杯水车薪。韩国千人平均的医生数量是2.2人,在发达国家之中是较低的水平,甚至比起我国都略低一些;而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的医疗力量,都形成了较为严重的透支;此外,韩国是全球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甚至一定程度上不需要这个之一,老龄化程度比我们常说的日本都严重不少。这些都意味着,未来几十年,韩国需要很多医生,远不是四千人就足够的。所以文在寅方面也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面松口,因为有些问题是不能不去面对的。
实际上,增加医学生数量对于医生也不是没有好处的事情,足够的医学生数量可以减轻医生的压力,而人数更多的群体,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其实也会更大;而在全球范围的实践也表明,医学生的扩招,对于待遇的影响,远没有想象之中那么大。只是即使在有这些因素的情况下,韩国医生依然这样选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韩国医生道德低下,自私自利吗?我并不认为一个职业的道德水平会和这个社会的平均水平差异太多,起码这次罢诊中急诊室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们没有参与。而从疫情之中,韩国医务工作者优秀的表现来看,这点也是不成立的。这样的群体问题,我觉得必须要从整个社会的视角去看,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许能感觉到一种集体性的身不由己。
当然,说这种身不由己与悲哀,未免显得有点奇怪,韩国医生的平均收入是韩国国民的五倍,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接近一百万一年的水平,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笔者这辈子显然没有机会达到这样的收入。只是这样的数据列出之后,笔者难免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的收入为什么这么高呢?
一般人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是他们的努力所得。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医疗工作属于强度很高而且复杂的工作,而且是社会必须的部分,所以理所应当的有较高的待遇;只是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种不一样的视角,那就是这些医生可以给资本带来足够的利润。
韩国的医疗系统,属于那种私营医疗占据绝对优势的,各项医疗领域的百分之九十,几乎都被私人机构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系统的出发点,必然是以资本运作规律来运行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典型结论,资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冰冷的铁律在一切领域都公平的运行着,它并不会因为医疗是现代社会之中的必需品就停止运作。所以即使韩国的疫情进入了二次爆发,即使有病人因为这次事件死亡,但是韩国的医疗界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他们选择控制医师数量,去保护资本的利益。
设置严格的准入门槛,来保障资本的利益,在很多领域都发生过这样的事件,西方国家的医疗领域就是极为典型的例子。在这些国家,医学院对于分数都有极高的要求,攻读时限也比一般的学科长,更重要的是,有着高昂的学费,这些东西共同铸成了第一道门槛;第二道门槛则是医师资格的获得,需要长期的实习,还有异常复杂的考试,同时,每年的名额还有限定。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西方国家成为一名医生,难度可以说是非常夸张了。
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严格的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生的水平,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结合确实提高了临床和科研的水平,但是正如我在另外一篇文章提到过的,高水平的医生无疑可以更高效的处理复杂的病例,但是在单位时间里边内,可以处理的病例数,并不会多太多。
所以,一旦过度提高门槛,虽然切实的提高了医生水平,但是很多人会注定享受不到医疗服务,这样的事情在这次新冠全球流行之中,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显然,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方案并不利于人民群众的健康条件最大化。从美国先进的医学水平和他们的人均寿命的不进反退就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但是与此同时,这样的方案利于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在控制总量,而这个产品又是必需品的场景之下,资本存在着巨大的操作空间。至于例子,无论是韩国的这次事件,还是美国的医疗保险集团,都足以证明这一点。而在资本主义医疗体系之中,医生扮演的角色,则是这个系统运作的关键。
在这里我并不想指责这些医生,因为正像我之前所说,这是一种身不由己。人类的道德并非是活在真空之中的球形鸡,而是切实受到社会各种因素影响的,其中,资本的影响可能就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这种道德上面的身不由己,或许可以归类成为异化的一种。异化这个概念在政治经济学与精神分析之中有很多讨论,对于这个概念各个学派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不过在这个问题之中,我们需要讨论的并没有那么复杂,单纯是资本构造的环境,对于道德判断的影响。
在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作为导向的医疗圈子里边,人的行为和判断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一个人从医学院到正式成为医生,都受到这种环境的扰动,指望他的道德一点不受干扰本就是不现实的,人类的道德本来就是在社会实践之中形成的,并不是凭空完成。在这种环境之中,判断模式和思考逻辑都会出现影响,显然韩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医疗圈子正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抗议的利益大于患者的利益这种判断,也毫不奇怪。说不定有人还会觉得,自己的抗议是为了患者利益的最大化呢。实际上,这样的选择未必利于韩国医生的利益最大化,但是他们依然不在乎。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笑?但是这却是在不同领域多次发生的现实,互联网讨论这种,经常有些“精神资产阶级”发表一些神奇的言论,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感到无奈,忍俊不禁的地方在于这些言论过于可笑,无奈的地方在于,这些人大多数并不是什么水军,而是真的这么想的,是在环境作用之下,切实产生了这些可笑的想法。这一点与韩国医生的事情,是高度类似的,在资本的异化之下,人是很容易失去自己的判断力,这一点,很多时候与智力无关,当我们接触的信息都开始失真,那么想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实在是谈不上简单。
在如此现实的情况下,指望韩国医生都像是白求恩大夫一样充满着国际主义精神,显然是一点都不现实了,个人的智力与能力,在席卷一切的大潮面前,并没有想象之中那么坚固。而作为医生群体发声的关键力量,韩国医师协会则是实质上主导了这次事件,当然了,名义自然是维护了医生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来说,它维护的是医疗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医疗既得利益集团本身。
这样的情况也是有原因的,医生的培养与流水线工作人员终究是不同的,医生的培养周期漫长,对于天赋有着比较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模式之下,很多医生的培养实际上是传统的师徒制,这样的制度之下,难免会存在人身依附这类封建残余;而医生不同于程序员,是一种周期很长的职业,老前辈的影响力自然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的既得利益集团,很容易以一种类似于中世纪行业协会的模式出现,控制医生数量,影响医疗服务价格,逐渐形成关门主义,都是行业协会的典型行为。结合这次事件,我们似乎又一次看到了历史以相似的形式重复。
只是马克思告诉我们,行业协会这种形式,在初期有助于生产力发展,但是很快,就成为了生产力的阻碍,这一点对于各种行业协会是通用的。而人类要面临的现实是,全球人口增长的同时,不断老龄化;医疗卫生的挑战多元化,不同国家,不同阶层面临的健康挑战差异明显;生命科学的研究虽然创造出来了璀璨的成果,但是边际效应显得越来越明显;医疗支出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为主要的负担之一,继续提升的空间越来越小;资本主义周期进入下行期,医疗系统的资金运作遇到巨大压力。
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医疗领域的生产力,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进步,那么人类多年以来,构造的医学体系,和这个体系构造出来的各种文明成就,都有可能化作梦幻泡影。这种情况自然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条路,从来都不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