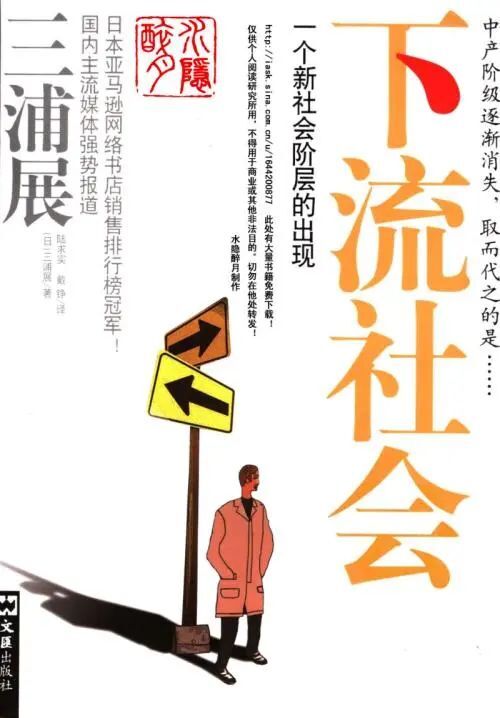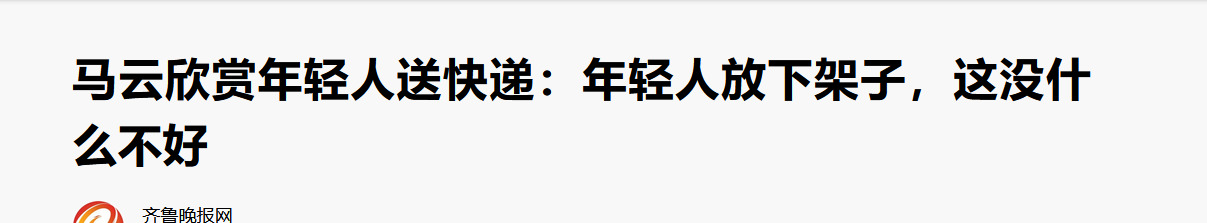文 | acel rovsion
大众在日常讨论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群的差异时经常会使用如80后,90后,00后等概念,虽然纯以年代划分并不特别精确,但关于世代模型的研究确实一直是社会和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文化研究中的世代模型一般会追溯到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卡尔·曼海姆,这源于他本人对集体无意识和集体心理状态研究的一种衍生。在后发国家风起云涌的变革浪潮中,短短二十年可能就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得每一个世代都具备共同的历史语境、生命体验,和在此之上建构出的自我认同。而这种自我认同又是极度排他性,每一个世代面对前后历史阶段的断裂中产生的异质性要素,要么采取否定和排他的态度,或者是将它想像成成自己熟悉的东西。举个例子,上一辈对这一代人的亚文化的态度要么处于极度不屑甚至认为幼稚,要么就是居高临下地猎奇,似乎能够让渡一些宽容。
著有《银河系漫游五部曲》的科幻作家亚当斯对这种世代认同有过精妙的吐槽:“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
不过就像我们开头说的,单纯以年代划分世代并不特别精确,在世代模型研究中,对在一个处于文化动荡期的社会中成长的青年称为“夹缝一代”,他们属于世代中的特例,他们特殊的亚文化运动和特殊心理状态是世代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这种处于夹缝中的特例包括德国魏玛时期的青年,美国嬉皮士青年,日本“平成废宅”,我国91-95后(这里的91-95后指代的更多是一种特征而不是精确的年龄划分)等等。
一战之后魏玛共和国的漂鸟运动可以看作一个典型。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等研究者认为青年人对于父亲的绝对反叛是漂鸟运动的首要特征,通过流行文化的方式体现表现主义的审美,将反叛诉诸于情绪与想象力。
当然,青年漂鸟(Wandervogel)运动本身是魏玛共和国文化内部不稳定的一种历史语境体现——在战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尸体上仓促凑成的政治体,经历了传统容克地主阶级和柏林中产阶级文化坍塌的瞬间,陷入历史夹缝的空位里,左翼运动和保守阵营风起云涌,同时孱弱的魏玛本身给予的共和政治承诺早就流于形式,政党政治的保守性和市民社会的自组织和激进运动激烈地碰撞。
而对于这时候成长的青年一代,他们既希望摆脱市民阶级价值观中保守和空想自由主义的束缚,又希望通过文化组织建立一个超脱性的共同生活空间。这个空间没有纲领,内部政治诉求和文化诉求混乱甚至自我矛盾,但这是历史夹缝之间野蛮生长的荆棘,想要瞥见夹缝透出的阳光,并为之无谓地挣扎。这和后工业时代初期的美国六十年代青年反文化运动的逻辑极为类似。
迷茫与焦虑是夹缝一代的特征,电影《摇摆狂潮》(swing kids)中就体现的是魏玛文化缺位后德国青年对于英美流行文化,尤其是摇滚乐的极度热衷,并且诉诸了一种带有反叛性的摇滚乌托邦的想象。电影表现了夹缝一代迷茫的核心,面对的是传统秩序坍塌后过剩的观念填充,同时对着上一个历史语境反叛,又对降临过快的新时代感到无所适从。
同时,夹缝一代的特征还存在的经济系统的缺位。我们回到东亚世界,三浦展有个概念叫“下流社会”,这是针对日本团块世代“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想象而来的,“下流”们在社会上普遍缺乏生活的欲求(相比于事业稳步上升的中流)。对生活以及事业上升的“期望”变成除却资本,品味等身份和阶级区隔方式之外的另一种区隔方式,对生活持什么态度也变成阶级表征了。
日本夹缝一代的实质上是泡沫经济崩塌前后,全球资本主义加速发展造成了阶级分化加剧,传统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走向不稳,甚至坍塌,大量年轻人要么劳务派遣,要么在拿着薪水不高的正社员工资,远达不到团块时代正社员年龄+万日元的薪资期待水平。于是总中流社会的稳定成长和路径依赖开始破碎,绝大部分人都开始趋于自我放弃或转移生活重心。
同时,平成时代廉价的文化工业品和工业社会撑起的基本生活保障。使得平成的年轻世代们可以用消费品,文化工业品和品味认同给自己制造一个完美的“自我舒适区”。阶级再生产的无望和无力感,让人选择回归亚文化的共同体内。
最重要的是,团块世代同时经历了物质匮乏和经济发展,在中流化社会形成初期具备的创业精神本质是对匮乏和贫富差距的恐惧。同时团块世代是趋于阶级上升稳态的,老老实实大学毕业当正社员,一步一步从课长开始爬。但这种阶级阶梯对于“平成废宅”,“下流社会"这种世代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夹缝一代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前世代稳固的生活模式和阶级阶梯开始坍塌,刚从这种稳固的普遍性中破壳而出的夹缝世代们,开始面对的是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经济和雇佣模式,感到无所适从。
而世代本身也蕴含着文化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问题,这里我把我国的夹缝一代特定在91-95这一个区间。中文世界的社会分层理论本身也是追随着社会结构转型来进行不断自我更新的,对于我国来说,诸如“X零后“这样的世代论是共和国产业快速积累期所带来的一种靠世代共同记忆区分的方式。各世代的共同记忆由于主流文化的快速变迁产生多多少少的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带来一种所谓的年代文化保守意识,而这种文化保守意识和共和国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生态有关,每个不同阶段的所处于的人情共同体是螺旋错位的。60后要么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干了一辈子,或平庸或优秀的成了这些体系的中坚,唏嘘着60后中那些敢闯的人所带来的传说;70后下海已经成了潮流,东西部的经济分野开始快速拉开,90年代制造业创业的发展积累了共和国第一代富人,公务员场流传着下海致富者的传说。
80后出生在文化初生期,西方文化快速引入,自由主义思潮初现,90年代末互联网初生和同样90年代的痛苦的对外历史,夹在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大部分人重复了前人的路,但依然有部分变革者,他们成了一代人津津乐道的互联网,商业,文化界敢言敢做的偶像。
90后大多承续了70前后那批人的财富积累,以至于90后尚未成为社会话题,就有社会学家高喊“世代积累的断崖”,他们是沐浴着消费主义文化和公共政治热情的第一代,也是当今互联网话语权的主导者,大多人均不想重复前人而似乎大家又有资本这样做。但是老中产凋零而新中产(文化阶级和精神认同)开始形成,由资本产生了第一次鲜明的阶级分化,社会上升阶梯门槛的提高,却在物质最丰裕的年代形成了实现阶级上升所需资源的匮乏。这些是我将91-95定义为我国的"夹缝一代"的原因。
如今的互联网上,这一代年轻人所关注的话题,如做题家被嘲讽,四大天坑专业的劝退调侃,奋斗逼和工贼的批判等,除却阶级叙事以外,正是极端路径依赖者的人间喜剧和对整个群体社会总福利的透支。
夹缝世代的年轻人面临的叙事,恰恰是父辈世代的极端裂变,父辈正好是国家经济创业的一代,他们整个世代的分化是父辈阶级积累的一个缩影,父辈们阶级积累的成果不同也导致了“期望”的分化。而这种期望带来了一个奇妙的比下流社会更荒诞的情景——你我似乎都在消费廉价的文化工业品来自我满足,无论是亚文化周边或是自媒体输出的价值观,但在这个自以为可以逃避的话语空间中,仍然存在消费能力带来的断崖。
如今的教育回报率对你阶级再生产的提升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资本回报率的威力,在进一步的市场经济化中被释放出来。资本的驱动逻辑变迁和规模扩大了好多倍的经济系统等等打破了上个世代带给你的“好好努力——上大学——找份好工作——你就可以立足——组成家庭到退休”这个世界观。
这使得夹缝世代面临着一个奇怪的迷思,个体主义意识萌发,但是集体意识上还保留着对传统稳定秩序的依恋和归宿感。这使得这个世代和前后两代人都无法直接沟通。经历着共和国从九十年代的迷茫到新世纪的崛起这个宏大叙事,这和前世代头上还悬着“西方”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历史语境有一些区别,而和00后们直接记忆在新世纪共和国,直接立足于大国语境的模式又不一样。
或者说前一世代立足于前现代性的共和国,后一世代已经立足于现代性共和国语境本身去探讨公共议题,而夹缝世代则在前后的创口中逐渐失去声响。
你的社会阶层也处在奇怪的夹缝中,前一世代的市民阶级面对着共和国最大的房产增值红利转型成租金食利阶级,或者面临着懵懂时期的移动互联网和大基建市场化环境,或者占据体制内最核心的岗位。
而夹缝一代面临的是高企的房价和追不上资产回报率和转型阵痛期的就业岗位贫乏,庞大的大都市进入成本,唯一一代独生子女的抚养压力。
而在下一世代,或许直接面对着转型成功和产业升级的经济形势,夹缝一代又变成了一个似乎从未有过的记忆与挣扎,而当你熬资历到老了,真正接班的或许是真正的共和国公民而不是一群焦虑的老人。同时未来的主流文化语境也不会包含夹缝一代那独有的传统秩序与现代性间的混杂文化。
包括夹缝世代本身也存在着父辈积累的断裂,比如一二线城市市民阶级的房产和本地社会资本,改开红利一代的后浪们,还有十八线城市和县城极为本地化的士绅们。
在社会权力和空间中边缘化,在历史缝隙中游走,仿佛本土性的陌生人,可能是各国夹缝一代青年的共同写征。当然,这篇文章不是制造焦虑或者鼓励人投机,相信在沉思录的读者中有相当一大部分群体处在本文所说的这个世代中,我们探讨所面对的历史语境,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明确我们是谁和我们准备处于什么样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