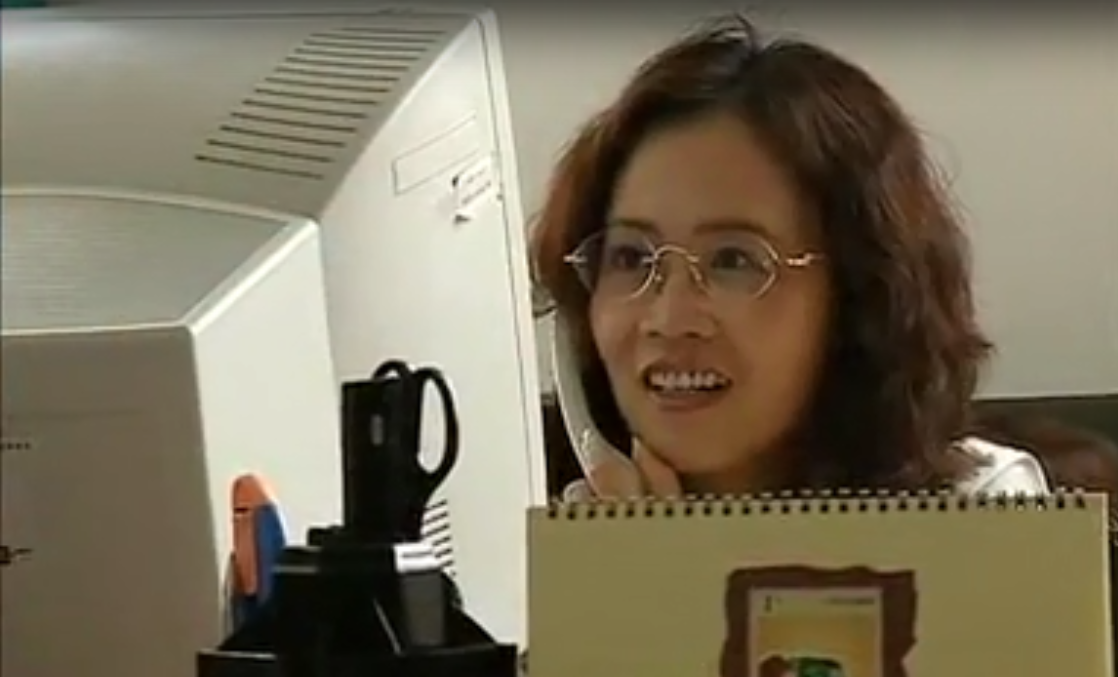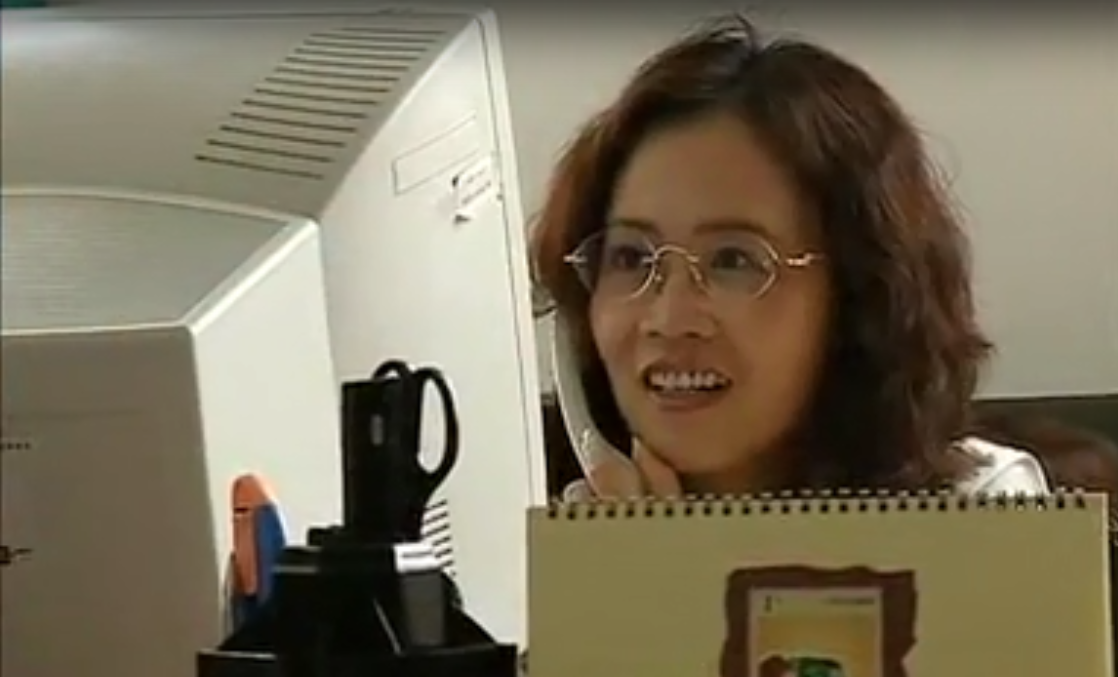1998年,41岁的赵本山凭借着“黑土派”短诗一跃而红,坐上了“小品一哥”的宝座:
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纵观世界风云,这边风景独好,谢谢!
在世界杯决赛中,法国队出乎意料地3-0轻取星光璀璨的巴西队,齐达内就此封神。
克林顿面对年轻貌美的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终究没有管住自己的裤腰带,犯下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因此遭到了弹劾。
回到国内,长江、嫩江、松花江都发生了特大洪水,受灾人口两亿多,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1660亿元。
在众多大事件中,有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人事变动:《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新闻部主任兼首席记者胡舒立辞职了。在这年四月,《财经》杂志正式发刊。
而就在1999年的第一天,扎根广州的《南方周末》首次发表了新年献词。43岁的主编江艺平撰写了新年发刊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其中特意提到了一句“透过记者的眼睛,我们奋力传递了昆明铲除恶霸的呼喊”。
此后,《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和发刊词成为了传统,每年辞旧迎新之时,他们的新年献词总是能一石激起千层浪。
只是江艺平未必能想到,文中的昆明恶霸孙小果不仅出狱了,还改名换姓成为了企业家。
这一年,风头正盛的《南方周末》和刚刚崛起的《财经》携手同行,畅想着中国新闻的21世纪。
而站在背后的江艺平与胡舒立,也距离“北胡南江”的名号越来越近。
1953年,胡舒立出生在北京,从13岁开始,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胡舒立参军、入党、下放,在苏北一所偏僻医院里待了整整八年。
先是当清洁工,再是进广播站播报新闻和医院通知,日子就这样一溜烟地过去了。
直到1977年,在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兴奋的胡舒立看到了曙光。在一年之后,25岁的她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
一切似乎理所应当。胡舒立的外公胡仲持是中国著名的编辑和翻译家,大外公胡愈之曾经担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新闻出版署署长,而母亲也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
不过出身新闻世家的胡舒立却从心底里看不起记者这个行当,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报纸只不过是传声筒,对此大失所望的胡舒立压根不认为新闻工作者能扮演好应有的社会角色。
而此时新闻系的学生大多把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没几个人打算在毕业后真正地去用新闻干预社会。
不过在四年之后,胡舒立改变了主意。此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正阔步向前,在活跃的氛围下,新闻记者成为重要的监督者和发声者。
1982年,29岁的胡舒立来到了母亲任职的《工人日报》,开始负责国际新闻的采访和报道。
而就在同一年,26岁的江艺平也告别了大学生活,进入南方日报社工作。
出生在广东的江艺平和北京人胡舒立的青春极其相似,当过知青,做过焊工,同样凭借着高考进入新世界。只不过,江艺平走入的是身处岭南的中山大学中文系。
凭借出色的才华,江艺平很快在报社脱颖而出。1984年,才入职两年的她就被老社长黄文俞视作“报社有史以来最有才气的女记者”。甚至单看文章,不看作者名,黄文俞就知道是江艺平的大作。
在临退休前,黄文俞特意叮嘱部下:千万别让她去当官!
不久,江艺平遇到了自己的另一位伯乐——左方,也就是她文章中常提的“老左”。
老左原名黄克骥,是个地地道道的老革命,16岁入伍当兵,上过朝鲜战场,文武全才的他复员后考进了北大中文系。
毕业后的左方在文革中是个相当活跃的造反派头头,甚至夺了省委机关《南方日报》的权。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年,左方并不招人待见,在日报社也只能做个看管资料室的闲差。
1983年年底,报社领导觉得左方面壁的时间够久了,于是召见他,希望他能主办个一周一期的报纸。
左方应下了差事,因为早就听过江艺平的才名,所以软磨硬泡之后,把江艺平从别的部门挖了过来。
最开始报社定下的刊名叫《南方日报-星期六刊》,但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名字太长,不利于传播,于是重新商量之后,改名《南方周末》。
在成立初期,看到别的报纸总有些“假大空”的感觉,敢说敢做的左方忍受不了,于是给《南方周末》定下基调:有可以不说的真话,绝不可以说假话。
在左方的设想里,《南方周末》要成为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的桥梁,科学民主的启蒙者。
1984年2月11日,《南方周末》第一期正式发行,头版刊登了《邓伯伯健步登上罗仙姑山》,详细报道了79岁高龄的邓小平巡视广东的一些轶事,打响了第一炮。
这一年,呱呱坠地的《南方周末》发行了7000多份,一时瞩目。
1985年,胡舒立写下的一篇关于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轰动一时。同年,她被《工人日报》派遣到了厦门记者站。在那里,长袖善舞的她结识了不少贵人,也为自己积累下了深厚的人脉。
也是在这一年,32岁的胡舒立接受美国民间组织“世界新闻研究所”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此时美国的新闻界运作已经非常成熟,在这里,胡舒立先后实习了三家报社,其中包括著名的《华盛顿时报》。
两年后,本可以留在美国的胡舒立拒绝了当地一家报纸的offer,回到了中国。
事后胡舒立回忆起了拒绝美国同行橄榄枝的原因:“想来想去发现自己最大的乐趣就是将自己的东西变成方块字登出来,让许许多多人看见,要知道中国有13亿人啊。而如果在美国当记者,其价值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1992年,胡舒立离开了《工人日报》,加入《中华工商时报》。但进去没多久,一次采访就彻底改变了胡舒立的人生走向。
在《工人日报》的十年里,胡舒立一直是国际政治记者,但到了《中华工商时报》,她的工作领域转成了金融和财经,“两眼一抹黑”的胡舒立一下子成了外行人。
1993年,报社要做一个金融改革系列的报道,于是就让胡舒立去采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采访完了之后,吴敬琏转头跟其他人说:这记者怎么不懂经济啊?
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想要谈论一个比较专业深入的话题时,必须棋逢对手才有得聊,否则就跟打乒乓球一样,对方总是在捡球,你玩起来也没意思。
怕胡舒立理解不了自己的谈话,吴敬琏给她列了一份书单,说你把这些都看完,说不定能明白我啥意思。
于是之后的一段时间,胡舒立没事就一边看书一边听采访录音,感觉全都理解得差不多了之后,才将稿件写好寄给了吴敬琏,后者这才满意。
这次采访仿佛打通了胡舒立的任督二脉,直到1998年离职前,她采访了丁望、萧灼基等国内一众经济学家,写出了多篇深度报道,并被冠上了“中国第一财经记者”的称号。
就在胡舒立春风得意的时候,远在广州的《南方周末》却遭遇了停刊危机。
此时的《南方周末》已经颇具影响力,发行量达到了百万级别,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邹启宇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发现阅览室里其它报纸都是新的,就《南方周末》已经被翻得卷了边。
当时文化部主编的报纸《文化报》发表了一篇长文,批判前部长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暗指其立场不正,散发着影射意味。
其实这和《南方周末》压根扯不上关系,但无巧不成书的是,同一时间发行的《南方周末》以比较积极的口吻刊登了一篇关于王蒙日常生活的文章,还附上了不少他的近照。
这让文化部有些恼火:我们刚批判他,你们就宣传他的日常,这不是跟我们对着干吗?
如果这事还不算严重的话,《南方周末》的两篇文章真正把它顶上了风口浪尖。
先是《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一文涉嫌泄密,抖出了不少秘密消息,引起安全部的不满。
随之而来的《袭警案》一文则更加严重,该篇报道讲述了一个颇为狗血的故事:一对不孕不育的夫妇找另外一个男人“借种”,被当地民警以卖淫嫖娼敲诈勒索,被敲诈的三人一怒之下,杀死了民警和他的儿子。
这篇文章曲折离奇,颇具可读性,但最致命的是:它是一个江西作家虚构的小说。而《南方周末》将其当做新闻刊登了几天,在传得沸沸扬扬之后,作家才打来电话,说这是编的。
左方的同事游雁凌回忆:《袭警案》差点给报纸带来灭顶之灾。
那几天左方夜不能寐,多次检讨,因为快到了退休年龄,所以干脆将《袭警案》一文的责任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
在多方的斡旋下,这才止住了《南方周末》的这场风波。
1996年,左方正式退休,40岁的江艺平成为了《南方周末》的主编,日后业内人员回忆起这段时光,通常将其称为“江艺平时代”或者“黄金时代”。
江艺平为人十分谦和,从不摆架子,与人交谈时甚至绝不会隔着障碍物,哪怕你的职位远远低于她,或者有求于她,她和你说话时都会并排坐在一张沙发上。
而且自己能够做的事,江艺平也从不麻烦别人,因为始终自己坐公交车上下班,报社给她配的司机曾经跟同事“哭诉”: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失业了。
1996年9月,《南方周末》准备扩大到24版,所以对内容的需求大增,而江艺平就开始从全国各地网罗优秀记者。
而正在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工作,曾经凭借《唐山大地震》等作品多次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的钱钢进入了《南方周末》的视野。
已经退休的左方亲自出马,邀请他参加《南方周末》的业务研讨会。此时报社的氛围十分自由,年轻的编辑们时常长发飘飘。
这倒不要紧,但因为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开会也时不时地迟到,加上供职于国内闻名的报纸,所以编辑们都带着点猖狂劲儿。
钱钢对他们的才华是认可的,但这种做派让曾经当过军人,十分重视纪律的他很不适应,所以直接拒绝了邀请。不久后,左方再次与钱钢相遇,并言之凿凿地表示:不来《南方周末》,你会后悔的!
被打动的钱钢最终改变了主意,不过他刚到任,就给大家推荐了两本书:《议事规则》和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意思很简单:我们需要民主,但也得讲纪律。
此后杨海鹏、孙保罗、方三文等人先后加盟,《南方周末》的队伍日渐壮大。
供职于《成都商报》的余刘文只看了两次《南方周末》就下定决心加入。当时三峡工程正在进行,全国媒体几乎都是一个腔调,而只有《南方周末》大胆地提出了一些其它的看法。
虽然江艺平平日里和蔼可亲,但一旦开始工作,就立刻从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战士,再加上这些各地优秀记者的加入,《南方周末》无论是从内容质量还是广告营收上都达到了巅峰。
他们既首次让孙小果走进人们的视野(《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还成为中国最早关注艾滋病的媒体(《艾滋病在中国》),他们为妇女奔走呼吁(《被拐女为什么不能回家》),也为农民工代言(《周立太代农民工泣血上书近百起工伤案陆续开庭》)。
《南方周末》也被称之为“新闻界良心”“弱势群体代言人”。
此时的《南方周末》,已经成为了新闻记者最向往的地方,新闻界“黄埔军校”的名声越来越响。在这里工作过的记者,日后大多成为了中国新闻界的精英。
甚至有一种说法,如果离开《南方周末》后在别的地方没当个主编,都不好意思说。
除了新闻理想,《南方周末》的广告收入也顺利破亿,风头一时无两。
创始人左方也坦诚地表示:“《南方周末》是我栽的树,但是在江艺平手里开花结果。”
正当江艺平的《南方周末》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45岁的胡舒立迈出了重要一步:离开《中华工商时报》,自己创业。
之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一个叫王波明的人找到了她。
王波明是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的儿子,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在留学期间,他交到了一批好朋友,看看这些人的名字:许小年、周小川、王岐山……,就知道王波明的圈子有多高大上。
回国后的王波明参与组建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并为后来证监会的创立出了不少的力。
1998年,王波明准备创立一个更加大众化的财经媒体,于是他找到了“中国最好的财经记者”胡舒立。
两个人看起来是“天作之合”:王波明在财经圈有资源有人脉,而胡舒立的业务能力早已得到了验证。
但胡舒立表示:合作可以,我的要求你必须答应。第一,每年必须投入两百万的记者工资。第二,内容写什么完全由编辑部做主,投资方不得干涉。第三,采编独立,广告商也管不了内容。
如果你是媒体从业者,你就会感受到这几条要求有多嚣张:左打投资人爸爸,右怼金主爸爸。
总之一句话:啥也别管,打钱就完事了。要知道,当年的北京平均房价还不到5000,每年200万的投入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胡舒立有自己的理由,在她看来,记者必须有体面的收入,才能够维持住职业自尊心,更好地抗拒外部的诱惑。而且她公开声明,“独立、独家、独到”才算是真正的媒体。
野心勃勃的胡舒立说到做到。在《财经》的创刊号上,《谁为琼民源负责》这篇深度报道将胡舒立推到了舆论中心。这篇文章直指上市公司琼民源虚构利润和财务状况,并把琼民源的骗局一一展示在了数万股民面前。
一炮而红的《财经》首期就卖了五万册。之后的《财经》越发凶猛,经常揭露股市黑幕和证券市场的腐败。
2000年10月,《财经》发表了名为《基金黑幕》的万字专题长文,矛头直指全部基金公司。
《财经》的依据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赵瑜纲的报告。报告分析了1999年8月9日至2000年4月28日期间国内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22家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大宗股票交易的记录,得出的结论是“证券基金有大量违规操作、违法操作”,制造虚假交易量,坑骗投资者。
10月16日,10家基金公司在报纸上联合发表声明,称《财经》有诸多不实之词。三天后,《财经》奋起反击,宣布自己的报道数据来源正规且可信。
当时有人给胡舒立打电话,大意是基金是新生事物,长远来看利国利民,要爱护,不要刚诞生就猛烈抨击。你批评一家公司可以,不要对着全行业机枪扫射嘛!
但胡舒立采取了“硬刚”的姿态,亲自撰文反击: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体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杨澜曾经问她:你这是断了别人的财路啊。胡舒立回答:但我保护了另一部分人的财路。
2000年初,江艺平卸任了《南方周末》总编辑,但报社依旧大步向前。三年之后,它获得了“艾菲广告实效奖”,成为第一家获得国际营销大奖的中国报纸。
2008年,《南方周末》又被评选为老百姓心中报纸的“最理想品牌”。
也是在这一年,不遑多让的《财经》营收突破1.7亿。而胡舒立因为敢想敢说的风格,被美国《商业周刊》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此时的她以啄木鸟自诩:这个社会要有喜鹊,也必须有啄木鸟,而《财经》希望扮演的,正是一只啄木鸟的角色,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但就在不久之后,胡舒立和王波明这对最佳拍档选择分道扬镳。
一方面,《财经》一系列激进的报道使得原先约定好的“投资人无权过问内容”岌岌可危。忍无可忍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下发文件:重大稿件必须由中心进行审核,否则无权发表。
另一方面,胡舒立也愈加觉得不公平,在更新后的《财经》编委会中,作为主编的胡舒立居然没有入选,甚至连《财经》的决策会议都不能出席。
而此时的《财经》正是设计中心旗下最赚钱的品牌,仅2009年上半年就为集团带来了五千多万港元的收入,但劳苦功高的胡舒立却享受不到这些红利。
2009年11月9日,胡舒立正式辞职。她这一走几乎带走了全部的采编团队,174人中有147人跟随她一起离开。
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在互联网的普及下,纸媒逐渐式微。
仅在2015年上半年,报纸广告的降幅就达到了32%。闲来无事读报看杂志的习惯,已经被刷手机替代。
疫情初期,《财新》周刊连续发布多篇深度报导,其中既有对相关事件来龙去脉的梳理,又有对病毒研究专家的采访,还有对疫情下武汉市民生活的关注。
在许多人手足无措、惊恐万分的疫情初期,站在一线的《财新》让读者了解到更多真相,不少人表示,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传统媒体的业务能力终于体现了出来。
在2月底,《财新》刊登了《两月来,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福利院发生连续死亡》这篇独家报道,揭露武汉社会福利院11位老人疑似死于新冠病毒的事实。
当晚,武汉官方公开声称“疫情期间造谣传谣,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
不过,就在三月份之后,中国战疫胜果初显,西方发达国家却纷纷开始拉胯,真的变成了“纵观世界风云,这边风景独好”。
而总是采取批评姿态的《财新》也在公众心中从“为民请命的斗士”变成“屁股坐歪了的公知”,由于对方方日记的支持以及对西方“群体免疫”和鲍毓明性侵案的误差报导,舆论迅速转向,《财新》从高峰跌落低谷。
再看微博的言论,胡舒立已经被很多人视作“汉奸”、“公知”和“反华分子”。
江艺平可能算是幸运的,2013年退休的她早已成为了新闻界口耳相传的传奇人物。否则以她当年在《南方周末》的气性,此时的处境未必会比胡舒立柔和。
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近因效应,越近发生的事情越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时候,我们只能记住别人最近做错了什么,却全然忘记他之前做对了什么。
《无间道》里有句台词:只有事情改变人,没有人改变事情。
大浪淘沙,《南方周末》和《财新》,江艺平和胡舒立,是非功过只能留给时间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