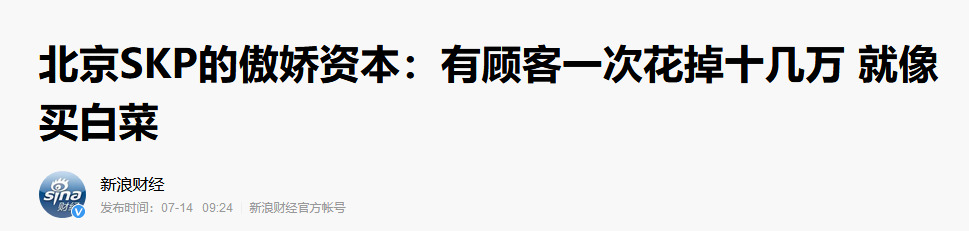文 | acel rovsion
最近,有关北京SKP商场不许外卖员身着制服进商场取餐的视频,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商场有权拒绝外卖人员进入吗?”的微博话题阅读量已达5亿,3万多网友参与讨论。
最早发帖的微博女博主网名曹导,并非真正的外卖员,只是体验了三天“外卖小哥”的不易生活。高温天里,跑了一下午的曹导接到北京SKP商场内一家奶茶店的订单,却被商场正门保安告知:不让进,要进可以披件外套或者把外卖员的制服脱掉。昨天,她把这段体验视频发布到网上,立即将SKP商场送上了热搜。
事后SKP方面声明称,疫情期间有固定位置取餐,外卖骑手在内的各工作人员需按规定统一从员工通道进入,一是为了防疫需求,二是商场较大,外卖员不了解环境,很容易在商场迷路,更耽误时间,所以规定了取餐路线。
据相关记者介绍,朝阳大悦城、东方银座、通州万达、国贸等购物中心,外卖员出示健康宝,扫健康码进行登记均可以进入。东城银河SOHO与SKP相似,疫情期间取餐需到专门外卖点等。而环球金融中心、达美中心等写字楼,楼内工作人员点外卖一率下楼取。
虽然商场方面说,这样的规定是方便疫情期间的管理,但显然,之前视频中“穿外卖工作服无法进入”这句话让争执点从“在哪儿取餐”转移到了“穿外卖服能否进店”。
外卖小哥的工作服到底和商场有着怎样的冲突?今天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展开聊聊。
之前我在《四川人和重庆人可不可能吃海底捞?》中写过,
对于城市布尔乔亚来说,维持城市运行的基础设施往往是看不见的系统底层。他们对于所处生活世界的想象往往是这样:所有资源都是既成的,电力是插座里自动发出来的,食物是超市里自己长出来的(哦,不对,现在说不定是外卖员用手搓出来放门口的),基础设施供给是理所应当的,文明世界所依赖的公共服务也是应该存在的。总之,基础设施的隐形和稳定,让城市布尔乔亚对城市充满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想象,与维持城市基础设施运营和以此而活的人群不会有多少共同语言。
一个城市的旧市民阶级的社会生活往往围绕着历史上基于遗留和自发聚集形成的街区和社区,属于熟人社会。而新兴市民阶级的社会生活围绕的是城市新的功能和商业地产的规划,这种新的社会基本组织结构属于陌生人社会,高端住宅里的人和隔壁园区的程序员可能在同一个城市综合体里面吃饭,可能还能见到外卖员在等单,但是相对于熟人社会的社区来看,这里充满了人群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当然,这种陌生人社会中的不同群体本质上还是处于一样的新兴商业模式中,都被融入了消费产业机器中。
这段论述仍适用于今天的话题,就像上面说的老死不相往来一样,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人对阶级身份的认知很容易被身处的公共空间同化,依据不同社会活动和交往秩序划为不同的圈层,圈层之间形成一种不言自明的区隔和排他。
虽然在我们的感性认识中,这个模式已经被消费资本包装的很完美,但是在不同圈层交叠的时候就会产生断裂,暴露出本来被掩盖的阶级剥削的象征——比如快递员这种支撑社会交往活动的底层工作者被当做不洁者被奢侈品消费购物中心制造的“体面”排斥在门外。
在经典的资本主义语境中,奢侈品消费购物中心类似于一种景观式的都市阶级制造装置,它制造的不是单纯的消费活动,而是进一步基于消费产业生产的身份符号交换、消费仪式体验和区隔感。它表面上提供的是对于商品物质和享乐的消费本身,实际上提供的更多是社会身份和价值意义的认同,甚至于伴随产生的价值和身份缺失的焦虑,对于物质的崇拜和消费行为本身变成了一种仪式。
奢侈品商场也有意识的将自身打造成资本主义幻境,它不仅只是消费活动场所,如同十九世纪初前后的巴黎拱廊一样,大量使用裸露的钢铁结构和透明玻璃制造的穹顶,用大量的汽灯制造眩晕感,拱廊下是平层地面上两侧排列的商铺,这种设计与其说是显示消费品本身的丰沛,更多的目的是制造侵略性的视觉奇观,将商场内的空间同外部的真实街巷区隔开来。欧洲早期奢侈品百货,比如哈罗德和老佛爷都是这样,往往将阶级符号歧视搞得非常明目张胆,甚至成为了一种默认的社会文化,它们乐于用古典建筑的奇怪给人制造惊颤的体验,商场就仿佛是给商品消费神教祭祀的场所。
而我国目前的奢侈品商场空间中却多了两重矛盾,一是商场要服从于现在的商业地产逻辑,要综合性的进行地产利用,并不可能向19-20世纪老欧洲那样把商业百货当公共景观来建设。综合空间利用和消费模式的扩展,以及人流量和消费力折算,导致商场必然会引入一些相对其消费定位来说廉价的餐饮和其他衍生消费模式,就形成了现在的购物娱乐消费一体的商业中心模式,这导致奢侈品商场想制造的区隔实际上无法存在。
二是共和国黄金发展期带来的商业神话和符号消费狂热,这些和社会主义的平等记忆是共存的,所以想制造区隔和高端体验的奢侈品商场陷入自相矛盾,它既不能像老欧洲百货那样诉诸已经默认的阶级区隔文化,还得在保证人流和保持高端两者间寻求均衡。直接对消费者进行统计歧视有巨大舆论风险(统计歧视是指比如根据地域,教育,工作,性别等统计资料对某些人群实行歧视对待),而奢侈品消费受众下沉也导致了对消费者直接进行统计歧视有很大的错配风险。
于是奢侈品商场就会选择区隔非消费者来达到目的,这种区隔包括让内部工作人员的举止、形象、语言模式和商场本身的视觉体验完全同化;同时把和这种体验完全不相容的象征符号,比如快递员等排斥在外,这种同化和排斥并不是针对人本身,而是针对会让它营造的体验崩塌的符号,比如美团的黄色工作服,于是就出现了奇怪的让外卖小哥把美团衣服脱了就能进的管理规定。
当然,并非所有商场都如此。只是这件事发生在SKP身上会让人觉得并不意外,北京SKP17年全球销售额第二,仅次于伦敦哈罗德,全球顶尖的奢侈品消费地,聚集北京最多的豪车,代表北京最顶尖的富人群体。这种奢侈品消费场所再怎么面向大众发展,本身还是会有无法抑制的制造身份区隔的趋势。
奢侈品商场是一个充满体面文化的空间,这个空间中,由外卖小哥这样的服务人员构成了消费系统底层。做为消费系统底层构建者,没有他们消费系统和体面空间就无法维系,但他们又不应该被看见,应该被被排斥于阶级装置制造出的体面文化之外。
这样的空间秩序要求形成各种毫无配套指示和设施的员工通道和排他性规定,但是外卖员又是一个负责各空间流通的职业,工作要求他必然要出现在这个体面的空间之中,于是,遭遇了“员工通道”,“指定聚餐地点”这种招来指去的劳动模式就和个体劳动尊严发生了严重冲突。在这个体面的空间中,所有人充当着水泥桩一般的构成要素,维持着这种空间权力的分配均衡。
但实际上,商场和办公楼寓所等不同,它甚至不是完全私有产权构成的领域,而是盈利性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中的使用权在不违反公共秩序的情况下理应属于公共品范畴,所以,为了制造身份区隔产生的体验设置和管理模式自然也应该受到公众的审议。所以,有网友说“我开个商场,外卖员不得随意进出,这点权力还是有的吧”这种理所当然的臆想并不合理。
当然,实践上这种公众审议对资本机器和阶级装置的冲撞实际上是有限的,尤其是网络上较为有话语权的核心受众说不定还很受用这种歧视性的区隔。
如何对抗这种体面文化主导的消费空间秩序呢?城市社会学的代表性学者大卫哈维的反抗诉求是让城市回到带有自组织意味和劳动者自治意味的带状街区去消解点状的资本空间的霸权,这种诉求在点状资本机器已经深深嵌入了现代城市空间和我们基于劳动分工和文化工业认同的可感知世界之后,显得前景薄弱。而另一位城市社会学代表性人物列斐伏尔或许可能更为清醒一点,他认为虽然消费文化被资本和符号机器包装的完美无缺,似乎不需要怀疑,但这套秩序的间隙中必然会出现矛盾激化,就像外卖小哥一样,必然会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揭开这层虚伪的包装,而此时,那些宣称资本主义已经完成历史终结的话语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否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