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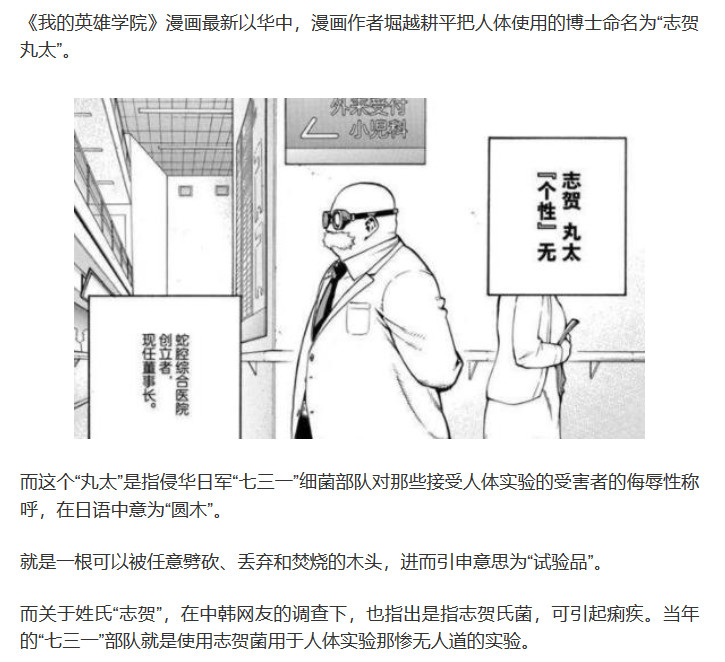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日本战后重建过程中受到了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以至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能够复活?以及更重要的,这种阴魂不散的思潮对日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这一类事物的出现,本质上是对内而非对外——并非刻意想要辱华或者想要测试国人的敏感度,而是精神污染带来的新民族主义宣泄——倒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出反应,而是我们需要明白这种行为的根源驱动力在哪。
此外,日本的再造的始发点应从1945年盟军最高官总司令部(GHQ)设立算起,但是这一阶段在Ian Buruma的《创造日本》一书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叙述,在本文里重新讲一次也不会有什么新意,基本上只能抄一遍Ian书中的内容,所以我们在此文中不会涉及。
▽
对于日本的战后再造,有两个关键词是无法绕过也不能忽视的:旧金山体系和1955体系。
所谓旧金山体系,指的是两个条约:其一是1951年九月日本在旧金山与四十八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和平条约,标示了日本即将脱离美国占领与代管状态,重获主权。其二则是旧金山条约的副产品,日美安保条约。
对于日本来说,和平条约与安保条约的签署,是否意味着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的确立呢?答案是否定的,两个条约本身都存在着无法忽视的缺陷。
首先,和平条约并没有让日本获得普遍谅解——签署和平条约的四十八个国家里,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没有被邀请参加此次条约签署与谈判,苏联虽然参与其中,但是最终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其次,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意味着美国获得了在日本保持驻军的权力,同时也带来了日本再武装化的要求。
为什么旧金山体系会排除亚洲地区的主要国家,同时提出日本再武装的要求?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1945年到1951年发生的大事中得到答案:首先是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48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其次是苏联在1949年获得了核武器;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最后则是1950年6月的朝鲜战争。
在冷战已经拉开序幕,美苏对抗正在升温的1951年,日本受到美国单独占领的后果显现了出来:在这个必须选边站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选择的权利。进一步的,旧金山体系并没有让日本获得置身事外的余地,事实上,日本的新角色和战前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在东亚地区制造冲突。
当然,冲突制造者这个角色也许听起来确实让人难以相信,但是直接证据我们可以在旧金山条约之中很轻松的找到:日本与苏联、韩国与中国的三处领土争议。
第一,日苏之间的千叶群岛问题。对于千叶群岛的归属,英美苏三国早在雅尔塔会议时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也即是苏联在日本投降后获得此地。但是当旧金山条约签署之时,虽然日本应条约要求宣布放弃千叶群岛的领土主张,但条约本身并没有将其所有权转移给苏联——虽然苏联在事实上占领了北方四岛。事实上,后来担任外交大臣的重光葵曾经提出过苏联交还齿舞与色丹两岛,划定日苏各半的分配方案,但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表示,如若日方放弃争议,那么美方将自动循此例获得琉球地区的永久主权,逼迫重光葵取消了这一计划。
第二,日韩之间的竹岛问题。在旧金山条约的早期版本中,竹岛的所有权被明确划分给了韩国,但是在49年12月,中国大陆建立人民政府之后,竹岛又被划分给了日本。在随后的50年8月的版本中,竹岛的归属权变得模糊起来——竹岛的所有权问题在条约中直接消失了。所以,最终日本签署的条约里,韩国获得了独立,但日本的领土范围却没有被明确厘清。
第三,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本身,是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时的战利品之一,但钓鱼岛所有权的转变,实质上是日本吞并冲绳群岛的副产品——钓鱼岛被视作冲绳的一部分。所以在二战结束后,美军从日本手中接收冲绳地区时,顺带也获得了钓鱼岛的控制权。而在随后将冲绳交还日本时,尽管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都表示异议,钓鱼岛仍被美军一同交还日本。
所以,既然自从旧金山条约签署之时,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定位就决定了这个国家无法与周边区域的邻国取得谅解并和平共存,这是否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了呢?
当然不是!除了旧金山条约之外,日本还与美国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而依照这个条约,日本在事实上成为了美军在亚洲地区最大的前线基地——不仅在当时是,至今仍是——驻日美军基地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朝鲜战争、越战、轰炸柬埔寨和老挝,甚至于后来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同样的,由于冷战对抗的需求,日美安保条约还对日本提出了再武装的要求——在前期,是指大量(75万)地面武装部队,但是这一需求很快改变了——核军备竞赛的开始使得地面部队的需求降低,海空军的需求上升,所以,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三军联席会议主席Radford提出了”新展望“政策,展开直接对日援助,以帮助日本建立能够配合美军作战的海空军部队。
进一步的说,旧金山条约与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从需要彻底改造的战败国,变成了美国围堵“赤色瘟疫”的最前线,世界局势与战略定位的变化,为1955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客观条件。
1955年二月,因为旧金山条约问题而分裂的左翼社会党再次合并,并且在大选中取得了三分之一席位(453席中的156席);为了应对来自社会党的挑战,由鸠山一郎领导的民主党与岸信介领导的自由党合并为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也即除了短暂数年在野之外,一直执政日本至今的自民党。社会党与自民党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对于1947年和平宪法,尤其是宪法第九条,永远放弃战争权力这一条款的态度:社会党拥护和平宪法,自民党则支持修改宪法,尤其是放弃战争权的第九条与涉及天皇的第一条。
自民党的出现,代表了右翼保守党在议会中占稳定多数并长期执政的1955体系的诞生,而鸠山一郎和前甲级战犯岸信介的合流,代表着“逆进程”的结束。
所谓“逆进程”,指的美国在冷战开始之后,出于反共的需求,对日本二战结束后到冷战开始这段时间活跃的左翼运动的清洗与反动,其目的自然是为了让日本能够在冷战对抗中为美国提供助力,而非相反。
事实上,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旧金山条约与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之前的1950年,美国在冷战压力下的战略转变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为了让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的发动起来,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马前卒,美国取消了日本的战争赔偿;原定需要解散或者拆分的数百家财阀企业和整体工业架构近乎完好无缺的保留了下来,同时获得了数十亿资金的注入,得以重新启动生产。
最重要的是,自1950年开始,所有在46/47年被“整肃令”和“解除公职令”清洗出局,并且宣布“永不叙用”的旧日本政府成员们迎来了春天:时任首相的吉田茂在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为近二十余万战犯被解除整肃,回归政府与政坛,与此同时,近乎相同数量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被赶出政府、企业与工会。
但是,美国对日本的规划,并没有获得日本的配合——即使是最右翼,最亲美的岸信介,也没有如他表面那般对于美国言听计从。最典型的例子,可以从日本的再武装过程中找到: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样,如果按照美国最初的设想,在解除了所有外界限制甚至获得了美国直接援助的情况下,日本应当建立一支至少三十五万,最好七十五万人的地面部队以便美国在有需要的时候进行征召。
而现实如何呢?虽然华盛顿在48年起便反复要求日方“尽快”进行军队的再建,但是在一心想要建设“东方瑞士”的麦克阿瑟的默许下,日方一直对此阳奉阴违。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即将卸任回国的情况下,日方才勉强改编了约七万五千人的“警察部队”。面对国务卿杜勒斯的步步紧逼,吉田茂甚至私下串通左翼社会党进行游行示威,以示并非自己不愿进一步扩张军队,而是民意不可违。
在美日双方领导层各有打算的前提下,作为美国与日方的博弈结果,美国在安保条约中获得了在日本无限期且不受限制驻军的权力,以及冲绳的管理权——换言之,冲绳将不会被作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交还给日本,而是将继续由美方直接管理。作为交换,美方不再逼迫日方进一步提高军队人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出于冷战对抗的需求,旧金山条约与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意味着美方在事实上放弃了“再建日本”的计划,改为仅控制日本对外的外交路线选择权,任由右翼旧日本军国体系内的成员们在美国画出的“民选+议会”蓝图上自行发展。
当旧日本军国政府的成员们再次回归他们熟悉的办公室时,另一个潜藏的问题也随之浮出了水面:日本在二战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说到战争责任,有一个角色是无法绕过的:天皇本人。天皇在日本军国主义兴起以及肆虐亚洲的这个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本人对此应该负担什么样的责任?
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阁下眼里,如果想要管理上亿个心智不全的亚洲人,那么让他们有一个可以效忠的对象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当澳大利亚,英国与苏联要求起诉裕仁时,最高司令官阁下便以审判天皇将会激起日本民变为理而拒绝了。而既然最高司令官阁下有意如此,有幸当了贰臣的旧日本帝国遗老们,如重光葵和木户幸一则迅速行动起来,开始将全体日本人和战争捆绑到一起——也即是所谓的“一亿国民总反省”。
同时他们也在所有即将被审判的战犯中串供,尽可能减少天皇在战争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最终,除了东条英机在审判时说漏嘴表示过“当时没人敢反对天皇”——这句供词在美方的配合下很快便撤回了——所有被审判的战犯们都表示天皇在整个二战过程中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橡皮图章。
发表了《人间宣言》,走下神坛的天皇近乎完好无损的逃脱了战后的审判,而天皇这一符号的存留,意味着旧的体制——也即是组织、策动并且最后制造了战争的旧日本官僚体系与政治生态圈活了下来,并且在55年以自民党的形式得以重生,形成了LDP政客-财阀-官僚(典型如MITI,MOF)的“三脚架”结构。
综合之前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当日本从美国手中接手他们有限的主权时,中苏已经从美国的盟友变成了敌人,日本也从美国的敌人变成盟友;战争责任人逃脱审判,回归权力中心;为了进行再武装并对抗“红色瘟疫”,外交的重心从和解变成了遏制,追溯旧体制战争罪责的动力彻底消失了。
顺理成章的,对于二战问题的讨论,在日本的语境内变得暧昧起来——尤其是日本经济腾飞之后,受制于美国的屈辱和对经济成就的自豪混杂在一起,酝酿出了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对“战争记忆”与“战争问题”的讨论变成了政党手中宣传的武器。
随着70年代的左派运动连接受挫,逐渐偃旗息鼓,右翼保守主义与新民族主义叙事开始占领舆论的高地。在保守主义与新民族主义的叙事中,广岛/长崎的核爆成为了为日本辩解的重要论据:来自核武器的创伤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日本曾经为其他国家与地区带来的创伤显得无足轻重。虽然在逻辑上两者毫无关系,但是对于“核武器受害者”身份的强调,极为有效的混淆了受害者与施暴者身份的界限。
同样的,日本战后的经历也为这种叙述提供了客观事实上的支持——如果日本做错了,那么为什么战后没有受到惩罚呢?既然没有受到惩罚,那么日本当年自然没有做错什么;受到核打击的日本,才是东亚战争的受害者!简而言之——对于战败深切反思,但是对于战争本身毫无反省。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如今这个特殊的时期,过秦论里的这段话,值得我们和他们反复思考。
-
CLG
-
兔瑟夫•托洛斯基
-
mitalos
-
囧
-
一只小狰狞Σ(°Д°;
-
修治
-
无敌
-
炎の炼丹宗师
-
bywuu
-
UrcheonBlaviken
-
紙風船
-
洛陽
-
yuan
-
みんなの椿婆
-
明相
-
H.I.C.M.S.
-
薛晓萌
-
开创未来
-
落木
-
Ddecline
-
树
-
暴风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