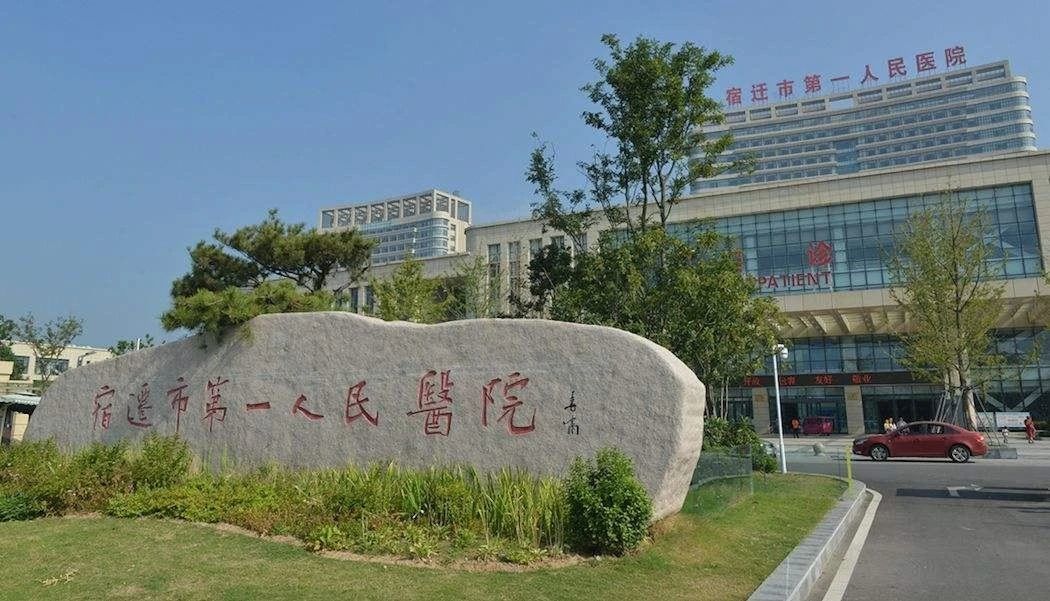作者:李墨天/陈晓荣
支持:远川研究医药组
2005年冬天,冰城哈尔滨搞出了一个大新闻:75岁的老人翁文辉患淋巴瘤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临床医院,最终因医治无效逝世。在医院的两个月,翁文辉花了550万元医疗费。
哈医大二院地处市郊,去看病的多是农民,一度被称作“屯子医院”。但在翁文辉住院的67天里,光是住院费每天平均就要花2万,还购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而根据病历单显示,专家前后为他进行了1180次“会诊”,平均每天20次,甚至在他去世后医院还开出了两张化验单[2]。
事情越闹越大,直接升级成卫生部牵头的联合调查,哈医大二院的财务出纳王丽丽随即被抓获:在2003年到2005年近三年里,她利用记账报账的机会贪污公款970万元,还给丈夫开了家医疗器械公司。后来,监察部门又从哈医大二院挖出了五件贪污大案,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处于舆论漩涡中的哈医大二院,各科室收取的药费与奖金直接挂钩,翁文辉的收费单上,前一天输了94次血,第二天又输了106瓶生理盐水和20瓶葡萄糖[2]。2006年4月,卫生部通报哈尔滨天价医药案,院长书记双双被撤职,一年后,王丽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那段时间,恰好是老百姓看病最痛苦的阶段,过度医疗层出不穷、以药养医屡禁不止,医保远未做到全民覆盖。而在同一年,本该在“十七大”前夕交卷的医改方案越改越复杂,又是启动全民讨论,又是全球征集意见,一直到了2008年11月,医改方案才向全民发布征集意见。
几天后,央视做了个节目,在黄金时间播出,主持人白岩松对着医改方案说:“都是中国字,连在一起却没太读懂。”
尽管方案并不完美,中国医疗体系仍然挽起裤腿,踏上了汹涌暗流中的第一块石头。这种背水一战的急迫其实来源于2003年的SARS,在那场席卷大江南北的疫情结束后,中央政府开始审视医疗卫生领域的长期欠账,政府卫生支出骤然提升,开始强渡这条难以轻易跨过的河。
17年后,中国医疗体系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中,迎来了一场大考。疫情爆发后,中国医疗系统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几乎所有的大型三甲医院都被紧急动员,最高峰时30个省市自治区有42481名医务工作人员前往湖北前线支援。这4万多人队伍,是中国医疗体系里的精华和尖子。
这是一次口罩下的检阅,也是一次对十七年医改成果的复盘。
01. 荆棘之路:非典之后的变革
2003年非典过境,国内医疗体系猝不及防。
彼时,鼠疫、天花这样的烈性传染病早已离我们无比遥远,肝炎和肺结核等普通疾病又不足以威胁到城市的运转。在创收压力下,很多综合医院取消了运维麻烦、利润微薄的感染科,这导致在疫情紧张期间,非典病人送进综合性医院后,由哪个科室收治都成了难题。
而从1978年到非典爆发的2003年,也正是医疗卫生支出急剧下滑的时期。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旗下甚至喊出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口号,而拿到尚方宝剑的医院纷纷解放思想,以药养医为代表的创收手段层出不穷,为日后的医疗乱象埋下伏笔。
直到非典给中国经济踩了一脚刹车,问题才被重视。在新一届政府的主导下,医改迅速上马,尽管参与各派时有争论,但在大多数领域的诉求都是相同的,比如在药品与医保层面,大家目标都是“降低药价”和“全民参保”,只不过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各个派别会有所分歧。
因此随后几年,药品降价和全民医保也是推动最快、成果最明显的两项改革。
医改启动后,最先提上议程的就是以药养医问题。顶层文件还在酝酿之时,敢想敢干的南京市率先宣布对全市200家医院药房进行托管改革:药房所有权归医院,但经营权转交给医药流通公司,上到医院院长下到采购员都无权插手购药,切断药品销售与医生之间的利益链条。
政策公布,雨花台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十多个药房工作人员,联名反对托管改革,甚至有人给院长打电话,“你要是搞药房托管,我抱着你从五楼跳下去[1]。”托管前,这家医院最多一天有3011个医药代表在走廊排队,医院不得不把每周四定为“医药代表接待日”。
而这仅仅是当地一家区级医院,全国其他医院的情况可想而知。
随着试点推进,政策设计本身的缺陷也逐渐暴露:虽然药房被托管,但接管的医药公司要保证医院收入不减少,药品销售的40%还要返还给医院,加之试点医院本就是规模很小的一二级医院,导致医药公司为了盈利必然低进高出,最终没能达到减少药品加成、降低药价的初衷。
2006年后,南京的托管改革试点到鼓楼医院、市一医院等三甲医院,一家医院的药品销售就抵得上100家一二级医院。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南京卫生行政部门成立了“药品集中托管中心”,负责全市9家大医院的药品采购,把活揽全在了自己手里。
看似医药分离,实则政企不分,改革又折了回来。类似的试点政策在全国只多不少,却总在执行中被带偏,作为“总院长”的卫生部门不愿牺牲医院利益,“医药分离”最终只停留在文件上。而同一时期,药品审批大跃进,刚降下去的药价又被曲线救国地抬了上去。
药品降价遇到一些挫折,但全民医保却势如破竹。2009年新医改前后,是药就批的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枪决,学术范十足的陈竺接任卫生部长,财政支出开始着重投向基层。随后几年,95%的国民被纳入医保,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例不断下降,是新医改立竿见影的成果。
不过全民医保也带来了新问题:2011年开始,医保支出超过收入,开源节流势在必行。
好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模式”,这次登上舞台的是福建三明。在新医改启动之时,提前进入老龄化的福建三明市医保资金已经严重穿底,2011年8月,有多年财贸和药监工作经验的詹积富担任副市长,借着全国医改浪潮,这个福建小城以每月一个文件的速度开启了“三明模式”。
文件背后的核心则是,在卫生部的基本药物制度的基础上,用“两票制”消除流通中的回扣环节,压低药价;同时,把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合,砍掉管理成本 ;另外,医生工资实行工分制,以缩小科室间的工资差距。
三明医改上马一年,医保基金的亏空就被抹平,药费在两年时间里从9亿直接下滑到5.7亿,詹积富一战成名。2014年,全国各地已经有超过160批人员到三明考察医改工作,是否要推广到全国,已经无需讨论了。
很快,尚有争议的“三明模式”被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轮番报道,由决策部门推向全国。2018年3月,“超级医保局”横空出世,医药价格、招标采购以及医保支付标准统合在了一个部门。人社部和计生委分管的三类医保也被归口到“超级医保局”的职责范围。
2016年3月,三明医改登上新闻联播
放大到国家层面后,政府面对药企的议价能力明显增强,原本涉及多方利益的“神药”也在一夜之间成为过街老鼠。在医保资金紧张的大背景下,各部门的行动空前统一,毕竟以前只是老百姓觉得药太贵,现在财政部也觉得药价有点高。
2013年底,首先来三明调研的不是卫生部门的官员,而是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问题的严峻可见一斑。不过官方报道里,只提到沿袭三明模式的医改成果卓著:医保压力缓解,药品大幅降价,医生收入提高,患者赞不绝口。翻译过来就是:一桌麻将,四个人都赢钱了。
但无论如何,医保的全民覆盖和药品降价,是医改十多年取得的实打实的成绩,无人可以否认。但医改之后,公立医院的医生工作压力加大,医患关系难以缓解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些改革触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体系,也往往因“条件不成熟”和“需要进一步研究”无疾而终。
长久以来,朝堂和江湖上对于医改的路线问题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是经济学家和媒体组成的“市场机制派”;一派以北大教授李玲为代表,主张政府调控为主的“政府主导派”。尽管双方针锋相对、频频交手,但在大多数层面,两者的诉求其实并没有太多差别。
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分歧,集中在一个缠绕着中国医改多年的问题:是做大做强公立医院,还是全力发展民营医院?
02. 宿迁浮沉:卖光式医改的困境
探讨这个问题,绕不开一个城市:江苏宿迁。
2003年,江苏小城宿迁在明星市委书记仇和的带领卖光了当地全部医院,从三甲级别到乡镇卫生院一个不留,就连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宿迁市人民医院也以7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上市公司金陵药业。不久后,宿迁医改以“卖光式医改”的称号响彻全国。
宿迁的实验成为了一个风向标,对它的褒贬也开始关系到公立医院改革的路线问题:市场做主,还是政府当家?
按照官方的说法,宿迁医改两年,人均门诊费用、平均住院日等硬指标全面下降,医院收入迅速攀升,非卫生技术人员占比持续下滑,还顺便解决了公立医院难以根治的顽疾——红包和回扣。在当时崇信西方经济模式的氛围中,媒体和学者对宿迁医改也是褒奖居多。
直到2003年8月SARS结束后,卫生部委派3名官员到宿迁展开调查,宿迁医改的二号人物、时任卫生局局长的葛志健收获了一句可以载入医改史册的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6]?”紧接着,李玲率课题组前往宿迁,得出了“老百姓医疗负担反而加重”的结论。
SARS平息后,中央开始自上而下梳理医疗卫生体系中的漏洞,在疾控中心和卫生体系上大局投入,并开始针对新一轮医改筹划”“顶层设计”,政府主导的声音全面盖过市场派,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抛出“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论调,市场派的声音几近偃旗息鼓。
宿迁医改的思路在于“管办分离、医卫分家”,即卫生部门交出医院所有权,只当裁判不当运动员,让看不见的手来促进公平。仇和曾与周其仁有过一次对谈,道出了“卖光式医改”的本质原因:宿迁实在穷,财政投给医疗的钱杯水车薪,不如把这个包袱交给市场[6]。
宿迁GDP常年位于江苏省尾部,卖光式医改的确减轻了财政压力。然而阴差阳错的是,非典过后,国家对医疗机构的投入开始大幅增加,没有一个公立医院的宿迁成了被遗忘的孤岛。以新医改起步的2009年为例,宿迁医疗系统拿到的财政补贴只有45.9万元,占江苏省的0.06%[1]。
改制之初,民营医院一度“形势一片大好”:当时,宿迁政府允许医院改制后申请“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备案,享受税收和土地政策优惠。但非营利性同时也意味着股东不能分红,2000年,新成立的钟吾医院接洽了20多位投资人,皆因“回报难以预计”放弃投资。
而长时间内,民营医院从地方财政得到的支持,仅为宿迁政府划拨的“奖金”,比如2010年,宿迁市人民医院拿到了综合考评第一,荣获奖金15万元。
宿迁模式的结局充满讽刺:随着新医改方案出台,针对公立医院的8500亿天量补贴呼之欲出,宿迁政府又打算买回当年7000万卖掉的宿迁市人民医院,报价超过10亿,却仍被控股的金陵药业被拒绝,不得不在2014年掏出了20亿,再建了一座公立医院。
新医院耗时三年完成,最终花费了26亿元。
按照顶级三甲医院的规模设计,床位2000张。当地的民营医院普遍陷入焦虑,担心政府能否对亲儿子和干儿子一视同仁。而在医院试营业前夕,宿迁模式的操盘手仇和与葛志健相继落马。仇和在忏悔书中这样评价自己:“光环笼罩,头脑发热,作风独断专行[19]。”
耗资巨大的宿迁第一人民医院,2017年
宿迁的试验后,公立医院的改革进入漫长的拉锯战,庙堂之上对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博弈也未曾停歇,被誉为最难啃骨头的公立医院改革,仍然方向不明。
之后的文件里,最明确的思路就是花钱、就是投入,但怎么花、谁来花却不甚明确。在中国,泾渭分明的对立往往都会在漫长的拉锯中被搅成一锅名为“深水区”的浑水,正如前卫生部某位领导对医改方向的措辞: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引入市场机制。
而在“既要又要”的胶着中,中国西南的一家医院却为迷茫中的公立医院改革指出了一条方向——它一直被高层忌讳和避免,却被无数基层三甲医院拥护,也在很大程度上勾勒了如今的中国医疗版图。
03. 华西样本:超级之外有超级
国务院打脸宿迁的同一年,新华社发了一篇文章,叫《全国人民上协和》。
记者在文章中这样描绘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幅景象:门诊大楼外,“出租躺椅”的小卖部生意兴隆,号贩子人头攒动,14元的专家号最高能卖到500元。而协和附近的几家医院,候诊大厅过了午后就空空荡荡,周边的社区诊所更是一天只能收治一两个病人[12]。

北京协和医院的排队人群,2012年
在SARS期间,群众和患者崇信大型公立医院的观念达到巅峰。当时,北京政府曾安排一些二级小医院承担接诊任务,但由于多年来对传染科的投入匮乏,一些中小医院在呼吸道疾病、重症抢救上捉襟见肘,不被病人信任,一度出现患者拒上急救车,企图跳窗逃跑等事件。
全国人民上协和的背后,是老百姓对优质医疗资源的用脚投票,也是中国公立医院大跃进式跑马圈地的一个缩影:凭借着公立医院充裕的现金流,优先激励医务人员、升级医疗设施,再依靠病源优势获得更多的收入,最终滚雪球般自我强化,让大型三甲医院越来越强。
而这条“先做大、再做强”的发展样本的奠定者,来自另一家“协和”——华西医院。
1937年,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内迁成都,与当地的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医,成为如今华西医院的前身。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华西医院都是一家典型的“三无医院”:无国家重点学科、无国家重点实验室、无两院院士。
1993年底,华西医院的胸心血管外科主任石应康担任院长,并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医生薪酬体系、到医疗设施投资、再到科研架构,石应康的每一步几乎都抢在了医改的前面[14]。
1994年,借着南巡讲话的东风,石应康在年度计划里写到,“用绩效考核干部的能力,用激励机制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在那个绝大多数医院还在思考“该不该赚钱”的年代,石应康一边对医务工作者实施内部股份制,一边花重金全国挖医学博士,用高额激励代替了大锅饭。
紧接着,石应康预见到了人口大省四川未来对医疗资源的迫切需求,便重金聘请设计团队,重新制定院区的扩建规划。同时,华西医院的医疗设备水平在90年代后就开始领跑全国,最有先见之明的一点是,在中国私家车还是稀罕玩意的时候,华西就设计了地下停车场。

华西医院鸟瞰,2015年
世纪初的10年,华西疯狂扩张,一跃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医院”,以至于媒体给石应康送了一个“砖头院长”的诨号。但在患者眼里,已是庞然大物的华西医院依然一床难求。
华西医院出动直升机转移脑梗病人,2018年
随着医保的逐步覆盖,华西医院几乎承接了中国西南绝大部分的疑难病患,基层病人也被“虹吸”到了华西。有了巨大的诊疗量,就意味着充足的样本,以及更多发现疑难病例的机会,这些都是高质量医学研究的富矿,进一步吸引医学人才络绎而来。
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医疗团队聚集在华西,把石应康的声望推到了顶峰,也在每个公立医院院长心中种下了一个“华西梦”。
但华西高光的背后,却是超级医院对周边医疗资源的强势挤占。一边是华西医院门庭若市,开着直升机运输重症患者,一边是乡镇小医院门可罗雀,基本收支都无法平衡。所以2009年新医改启动,公立医院的扩张遭到批判,此后近十年,顶层对医院规模的限制有增无减。
但政令之外,公立医院心照不宣的维持着两脚油门一脚刹车的节奏,一个个庞然大物拔地而起。
在另一个人口大省河南,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几乎复刻了华西医院的崛起之路:从千金求将、加床盖楼,到顶级医疗设备一应俱全,郑大一附院用10年时间走完了华西医院的的20年征途,从一个省内的二流医院,直接跨越到了收入过百亿、床位上万张的“宇宙最大医院”。

郑大一附院鸟瞰,2018年
郑大一附院的发展史,几乎是华西发展史的复刻,简单来说就是三点:一是给予医务人员高激励。二是大手笔投资医疗设施设备。三是以充足病源驱动医学研究。当然,缔造郑大一附院的,也有一个类似石应康的灵魂人物,他就是从1984年就在这家医院工作的阚全程。
但这种“超级医院”对周边地区的医疗资源、患者和医疗费用三者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让本来已经很不平衡的医疗资源分布更加不均匀。2015年河南两会期间,人大代表阚全程在发言时,有省领导当场向他喊话,“拉乡镇的兄弟医院一把,让老百姓能在家门口治大病。”
中国医改的复杂性在于:庙堂之上,卫健委是公立医院的亲妈,也是财政包养医院的支持者;人社部恰好相反,对医院扩张始终警惕;发改委操刀医改,哪边都不好得罪;财政部负责掏钱,哪边都是无底洞,而江湖之下,老百姓既要物美又要价廉,还得态度好。
对于医疗服务来说,廉价、便利、高水平,组成一个不可能三角,因此天然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在非典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公立医院+全民医保”成为中国平价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即使“超级医院”最强力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而市场机制派寄予厚望的民营医疗体系,这些年做的究竟怎样呢?
04. 水至深处:医疗供给改革的困局
2013年,一篇自称“医疗从业者”所著文章在互联网广为流传,作者高举市场化大旗,在结尾写到:卖掉协和医院,是中国医改成功的开端。
但没过多久,中国青年报以政府主导派的视角发文回击:《卖掉协和将是新医改的失败》。一个官方背景的媒体出面反驳一篇网文,实属罕见。大概是因为“卖协和”的争论又一次捅出了那个核心问题:中国的医疗到底有没有过市场化?到底需不需要市场化?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5年宿迁医改被打脸,是主流学界认可的中国医疗“市场化”的时期。这27年里,全国卫生总费用增长了77倍,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增长了200倍。但同期,医院数量仅增加了101%,医生数量增加了88%[6],有些年份甚至在下降。
这背后是政府派也不得不承认的问题:医生的供给并没有市场化。
即便在宿迁模式里,医生的供给也受限于“管办合一”的体系:院长招聘医生受到编制规定、招考制度规定等多方面的限制,甚至考什么也要由地方人事主管部门决定。医生的考评、职称则与公立医院紧紧挂钩,换句话说,一旦医生离开公立医院,便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断崖。
2010年,权威部门曾推出了一个对社会资本友好的文件:《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4年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出台,把社会办医上升到了产业政策高度。2019年,超级重磅《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面世。
但在中国,很多行业的“大力发展”,最终都逃不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规律:决策层期待中的良性市场参与主体出现的太晚,太少,民营阵营中只有武汉亚心、厦门长庚、北京和睦家等少数几支独苗勉强能拉出来做代表,反倒是邪恶的“莆田系”却遍地开花。
此后,改革思路由花钱转向治理,开始推行“分级诊疗”与“多点执业”,一边引导患者有序就医,下沉就医,一边打通医生自由流动。但在实际落实中,大医院医生本就工作量剧增,小医院医生没机会出去,多点执业搞不下去,分级诊疗也是向下容易,向上困难。
从表面上看,截至2018年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达到45.9万个,占比46%;社会办医院数量达到2.1万个,占比63.5%。数量虽多,但基本上都集中在口腔、眼科、皮肤等专科领域,大型综合医疗机构少,有名的更少,这导致民营医院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存在感并不强。
尤其对老百姓来说,无论市场机制有多少优点,超级公立医院都是患者在死亡面前的最后选择。
而在追赶公立医院的路上,民营医院体系愈发力不从心。医疗是一个资本密集行业,投建一个大型综合医院,平均每张床位的投建成本已经在50万元甚至100万元以上,一个县级综合医院的投入就需要10亿元以上,这使得很多社会资本只能龟缩一隅投建专科医院。
中国社会办医的江湖中,一直有“四大”的说法:华润系(华润医疗+华润健康)、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北大医疗产业集团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这四大办医力量背后都是富可敌国的央企和大型民企,但面对动辄几十亿的投入,仍然力不从心,建树有限。
民营医疗体系发展的长期困境,并没有削弱市场机制派的持续努力。2019年6月12号,十个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各地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文件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
但6个月后,似乎即将进入发展快车道的社会办医,以及可能被迎来“限制”的公立医院,突然遭遇了一场无法事先预知的疫情检阅。
05. 紧急动员:一场突如其来的检阅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役中,大型公立三甲医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湖北几乎所有的公立医院的医生,都冲在了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其中金银潭、协和、同济、中心医院等医疗机构的情形更是牵动无数中国人的心。在压力最大的1月底2月初,大量医生坚守岗位,甚至在缺乏防护用品的情况下继续工作,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而在各省支援湖北的大调兵中,全国各地的公立“超级医院”们更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甚至出现了“东齐鲁、西华西,北协和、南湘雅”四大公立医院会师的情景。在支援湖北的几百只医疗队和4万多名医护人员中,大部分都来自军方和公立医院。
民营医院并非没有参与抗疫。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统计[11],民营医疗机构先后有259个医疗队共计3984位医护人员前往湖北支援。但由于民营医院在学科设置上的短板(专科多,规模小,呼吸科配置几乎没有),他们发挥的作用跟公立医院无法相比。
毫无疑问,在这场口罩下的检阅中,公立医院是最令人敬佩和称赞的方阵。
作者:李墨天/陈晓荣
编辑:姚书恒/戴老板
数据:远川研究医药组
[1]. 大国医改,朱幼棣
[2]. 病人住院67天花掉140万,医院称少收病人费用,新京报
[3]. 医生过度治疗已成全社会风气,中国青年报
[4]. 聚焦医改十余年:政府派与市场派之争已久,中国新闻网
[5]. 宿迁医改之路,中国卫生产业
[6]. 病有所医当问谁:医改系列评论,周其仁
[7]. 政道:仇和十年,包永辉/徐寿松
[8]. 江苏宿迁首次回应卖光式医改,中国青年报
[9]. 江苏省宿迁地区医改调研报告,李玲
[10]. 李玲:中国的医改这些年做了什么,新浪财经
[11]. 编外的医者:非公医疗抗疫纪实,财新
[12]. 全国人民上协和:老百姓看病为什么非要上大医院,新华社
[13]. 解密华西,桂克全
[14]. 华西往事,八点健闻
[15]. 卖掉协和将是新医改的失败,中国青年报
[16]. 石应康遗体告别,讣告称其使华西医院成为重症国家级诊疗中心,澎湃新闻
[17]. 公立医院扩张: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财经
[18]. 中国医改评述,供给侧改革是关键,叶志敏
[19],人民日报红船观澜:常思责任莫顶“光环”,人民网
精选留言
-
姚旭作者
-
萍水无踪作者
-
🎀一個胖紙💤作者
-
F T作者
-
`Joe作者
-
仁远作者
-
蒋志强作者
-
PenG!作者
-
张宇洋作者
-
Fantasy作者
-
鹿子野作者
-
鱼🐟作者
-
山海为远作者
-
莫失莫忘作者
-
徐曼丽作者
-
加文💯中考培优作者
-
蓉城流浪作者
-
慕泽作者
-
姜姜🍊作者
-
墨泉作者
-
那个谁作者
-
BruceShen作者
-
通者达也作者
-
A 默默等待作者
-
zelongzhu作者
-
alps作者
-
王JiangBo作者
-
Y.rM作者
-
逍遥师兄作者
-
🐻玩具熊🐼作者
-
唐宁九作者
-
[Grin]作者
-
巴塞罗那的梦作者
-
孔方兄作者
-
朱济珉作者
-
文智作者
-
Minqi作者
-
悦黑疯高作者
-
燕铁衣作者
-
剑雨作者
-
勇作者
-
不是小料作者
-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作者
-
Dandy-6ᴮᵘⁱᶜᵏ作者
-
木子哥作者
-
Robin作者
-
郭禹辰作者
-
Lebron作者
-
肖韶华作者
-
番茄妈作者
-
Li莎😂🐳🍋作者
-
刘君豪作者
-
*晨作者
-
锦时作者
-
雪松作者
-
🚢本岸作者
-
Wave.W作者
-
融资顾问 王生作者
-
老司机作者
-
王龙作者
-
欣然作者
-
东风快递到你家作者
-
Comer作者
-
得俊作者
-
DJ作者
-
小神和他的朋友们
-
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