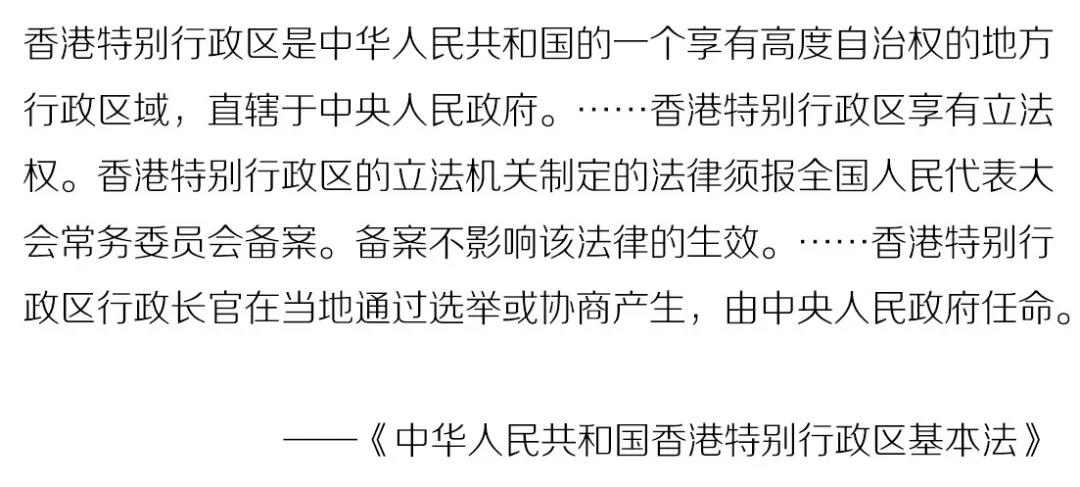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二十五岁的时候就知道:人的解放只能是现实的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去争论这个人是犹太人、英国人、德国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经验生活、个体劳动、个体关系的个人,“人的解放”才有意义。(《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追求解放全人类的马克思,传统政治学的终极目标始终力图追求一种“善治”,但是,并不是每个政治学家的理论都会指向这种对“善”的追求。
比如,在卡尔·施密特那里,政治只要区分“敌友”就可以了。没有敌人,那就生造出来一个敌人,让整个社会都去仇恨、蔑视某个群体,社会将会自然地团结在一起。
但这样的“团结”,也许往往只是为了更残酷的仇恨与杀戮。
后来,施密特的这套理论成为纳粹德国种族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思想来源。虽然施密特本人对纳粹假借生物学名词宣扬的那一套种族主义论调毫无兴趣,甚至为此差点丢掉了性命。
马克思也许不会想到,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网络写手,竟然会简单的用一个“蠢”字来概括一个城市一整代的青年人,并据此大言不惭地讨论“这座城市还有救吗?”
施密特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位青年人心中的愚蠢的“敌人”与高瞻远瞩的“我们”,竟然是同处于一个现代国民国家(nation state)的同胞。
从来,“愚蠢”的从来不是被草率地打上各色标签的犹太人、英国人、德国人或是哪个城市的人,而是这些自作聪明的定论者。
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眼中,从来没有“愚蠢”与“聪明”,只有沧海桑田的演变。
01
不可否认的是,1967年香港那场风暴的底色确实是一场反抗殖民统治的抗暴运动。放在全球历史的视野之下,这场由香港左翼知识分子掀起的运动,无疑是全世界“去殖民化运动”的重要一环。
自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就成了大英帝国国王的领地。对于这些海外的殖民地,英国会派遣一位“Viceroy”进行管理——这个词汇的前半部分“vice”来自拉丁语,意思是“副职”,后半部分“roy”则是法语roi(国王)的改写。
通常,这个词被译为“总督”,实际上,它相当于宗主国的君主在殖民地的化身。以民族主义立国的西方殖民者不会承认殖民地的“异邦人”与他们一样享有民治、民有、民享的权利,所以,殖民地的总督和他的政府在当地几乎有着不受约束的大权。总督名义上接受国王的任命,以爵士的身份宣誓对王室效忠,总览立法、行政、司法权力,除了不能世袭罔替以外,几乎与资产阶级革命前英法的“绝对君主”相侔。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放松了对已经形成了各自民族认同的“自治领”的控制,承认他们的国民可以像英国本土的民众一样选举自己的议会,产生自己的内阁,而总督则像英王一样作为象征“垂拱而治”。渐渐地,大英帝国被“英联邦”所取代。
但是在没有形成“民族”的香港,这种中世纪最后几年的统治方式却一直延续到了新时代的门槛上。
1960年代初非洲的解放宣告了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在遥远的东方,不论是港英当局还是普通的香港民众,开始逐渐意识到,旧的殖民体系已经走到了它历史的终点。
1966年,当全世界掀起一片红色的浪潮的时候,贫困、腐败和混乱的社会管理体系正在困扰着这个繁华拥挤的殖民城市。对殖民主义的切齿痛恨,对自己文化根脉的追寻,和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位置的探索,成为香港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不竭动力。
这一年,来往于九龙和香港岛的“天星小轮”突然宣布将头等票价从2毫涨到了2毫5分。谁也没想到,这样一次轻微的价格调整,却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
4月4日上午11时,一名青年坐在爱丁堡广场码头开始绝食抗议,他的衣服上写满了口号。很快,更多的青年聚集在他的周围,示威者们点燃了汽车占领了整个街道。最后,在驻港英军的帮助下,港英政府才勉强把这次暴动弹压了下去。
4月9日,300多名青年人站上了港英当局的审判台。尽管港督戴麟趾和首席按察司何瑾等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坚称,“经济上遭受挫折,社会贫富悬殊”是造成这次骚乱的根本原因,但是人们还是普遍相信,这次骚乱是对英国殖民当局一次激烈的政治抗议。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戴麟趾照例主持华人政务官选拔面试。当时,他向一位出身贫寒,没钱读大学,预科班读完后就在药厂做推销员的面试者发问道:
“你认为本届港督最大的政绩是什么?”
年轻人思忖了片刻,抬头看着金发碧眼的港督,说出了他心中的答案:前一年旱情中,香港城市供水断绝,戴麟趾亲自拨通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还亲自跑到广东,与地方政府接洽珠江、东江向香港的供水。他认为,这才是这位港督任上,最大的政绩。
香港的自来水管流出清澈的珠江水的那一刻,殖民政府的社会控制体系开始渐渐发生了松动。这可能是一场漫长的社会剧变的开始。
戴麟趾轻轻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勾,并记下了这个名字:“曾荫权”。
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初那几年,红色的怒潮席卷了整个世界。在日本,“赤军”占领了长野县的浅间山庄,绑架山庄工作人员长达十天,这些青年人的父母拿着高音喇叭哭喊着“毛主席已经会见了尼克松,你们的任务完成了”,也不能让这些狂热的青年人放下手中的武器。而在法国,青年人占领了巴黎,总统戴高乐不得不潜出首都,去向驻扎在边境的军队寻求帮助。
1967年的香港,作为大英帝国在亚洲最后一块殖民地,不可避免地走到了这场风暴的中心。
1967年1月,23岁的曾荫权正式成为港英政府的“二级行政主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一系列劳资纠纷的“星星之火”,渐渐演化成“六七暴动”的冲天巨浪。
▲1967年香港街头对峙的双方
就像日本、法国,乃至祖国大陆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人一样,香港的“革命青年”也渐渐彻底失去了控制:他们到处安放炸弹,对稍有异议的社会名流动辄施展暴力,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人林彬和他的堂弟竟被当街烧死在车内;而时任《明报》社长的金庸也因为收到死亡恐吓,而不得不暂时离开香港。
直到当年12月中旬,中国总理周恩来出面严厉谴责香港左派的“炸弹风潮”,这场风波才渐渐平息。
经历了1967年的风暴,港英当局也意识到,远远落后于时代的统治方式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1967年港英政府一开始面对风波的粗暴手段以及后来的束手无策,使得戴麟趾港督生涯的后四年都不得不为“挽回民心”而奔波。
1967年之后,港英当局一方面大力提高社会福利,推行“民政主任计划”,分区收集民意,沟通“官民”关系;推广八小时工作制,兴建廉租屋;发展交通网络。另一方面,当局还举办了两次规模庞大的“香港节”活动,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来提升居民的文化归属感,缓和日渐尖锐的社会政治矛盾。
风暴之后,在香港人的努力下,中文也渐渐取得了在香港社会的地位。从1969年开始,市民可以用中文拨打电视台的热线与政府官员交流意见,中文报章上的内容开始被当局重视,到了1972年,第一位使用中文的行政局议员钟士元终于走上了讲坛。
香港人用他们的抗争,终于松动了大英帝国笼罩在他们头顶的重重灰幕。
02
1971年10月,戴麟趾离任,54岁的麦理浩正式被英国女王任命为香港总督。这位担任过英国驻厦门、福州和汉口的外交官,曾经孤身独闯日军会所,早年间在马来西亚学了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可以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外交官,而不是一个“久历封疆”的殖民地官员成为新的港督,似乎说明,从白金汉宫到中环的总督府,乃至香江之畔的每一个香港人都认清了这样一个现实:这片土地上数百万人,不能仅仅作为英王的“臣民”,卑微地活着。
11月19日,麦理浩穿着殖民地传统官服,乘船横渡维多利亚港,在皇后码头检阅了驻港英军。而此时,香港“船王”董浩云的“海上学府”正停泊在青衣岛和昂船洲之间的海面上,进行最后的装饰工作。
董浩云可以说是那一代香港商人的一个成功的代表:1949年从上海辗转迁居香港以后,董浩云的生意几起几落,后来,他抓住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东西方之间航运需求大增的机会,做成了几单帮助美军运送军火物资的“大生意”。很快,董家开通了香港与欧美间的定期航线,渐渐成了仅次于包玉刚的“船王”。
生意做大的董浩云,在香港、台湾和外国之间辗转腾挪,发展自己的船运帝国之余,渐渐开始关心起香港的教育事业来。
1971年,董浩云花了230万美元,买下了一艘航行在大西洋两岸的邮轮。这艘“伊丽莎白皇后号”邮轮全长314米,排水三3万8千吨,可以载下两千多名乘客和一千多名船员。董浩云想把这艘船改造成一座航行在海上的高等学校——他相信,这将是一艘改变香港文化史的“海上学府”。
1972年1月9日,“海上学府”试航前六天,各项调试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董浩云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旅港期间,仍以头寸忙,修理‘海上学府’忙,日来为赠送港、日、台、新地区五名(一共20名)奖学金而忙。”
但就在这天,董浩云突然接到了正在“海上学府”召开会议的长子董建华打来的电话:“海上学府”突然发生大火,这艘承载了他教育梦想的豪华巨轮从起火到烧毁的过程,一字字打入“船王”的心头。
“欲哭无泪”“悲愤莫名”,在那一天的日记里,董浩云重重地写下了这八个字。
坐在逃生的小艇上,回首望着熊熊燃起的大火,34岁的董建华经历了他事业的第一次挫折。拨通父亲电话的那一刹那,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这位“七七事变”当天出生在上海的“少船王”,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开始颠沛流离,逃亡、求学、创业、守业,到如今,还没有哪一次的失败能如此剧烈地直击这个年轻人的心灵。
事后,警方调查认为,这起大火实际上出自人为,但究竟是谁放了这把大火,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燃烧的“海上学府”(图片来源:星岛日报)
不久之后,代替“海上学府”的“宇宙学府”重新提上了日程。在这座建在海上的高等学府里,学生们将跟随这艘邮轮航行在五洲四洋,在漫长的航行中学习知识,增进见闻——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香港的精英阶层从来不吝在教育上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力。
“精英”们热衷发展“精英教育”的同时,戴麟趾、麦理浩两任港督积极推动的“义务教育”也颇见成效,1971年,港府就已经推动落实了“六年义务教育”,1978年,“九年强迫免费教育”也在全港推行。
义务教育不光是让年轻人能读能写,还包含着公民教育、社会意识培养等一系列重要的任务。此时还在“大革命”中的中国大陆,后来改革开放事业的第一步,也是全面恢复城乡的义务教育。
除了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民生也成为港英政府积极关心的话题。
1967年的风暴让港英当局意识到,如果不能舒缓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香港将渐渐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火山口。
在1972年10月,麦理浩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重磅推出了“十年建屋计划”。这位新港督计划用十年时间,耗资80亿港币,由港英政府出面,修建容纳180万人的“公屋”。1976年,“十年建屋计划”正式开始启动,到10年后的1987年,这项工程虽然大有成效,但仍然只容纳了150万人居住,距离180万的预计目标有着高达30万的巨大缺口。
后来,“十年建屋计划”发展为“居者有其屋”计划,至今是港府积极推动的重大民生工程项目。在“寸土寸金”的山海之城,航运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一天天推动着经济的膨胀和人口的增加,这个历经坎坷的计划一直为香港居民提供着大量的廉价住房。
麦理浩赶上了好时候。在他在任的五年,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让香港迎来了经济腾飞的机会,而源源不断涌入的财富,不但为民生工程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大大高涨了香港商人们的投资热情。
这座城市在吸纳着来自全世界的财富,也在寻找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
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香港左翼团体举行了盛大的悼念仪式,港督麦理浩也亲赴现场敬献花圈。
1979年,邓小平在深圳河的对岸画了一个圈。麦理浩也在这年来到北京,向邓小平提出了新界续约的问题。
邓小平给他的答复让这位英国官员有些手足无措:中央政府将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但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又说,“请香港投资者放心”。4月4日,港督乘坐着第一班“港穗直通车”失魂落魄地回到了香港,在火车站,他只对香港商人和记者提起了邓小平的后半句话。
这一年,保守党一批“后座议员”到访香港,他们听到了中国政府将要收回香港的打算,其中一个名叫彭定康的议员私下里向麦理浩建议,可以在香港推行“民主”改革,至少可以迟滞这个行程。
麦理浩看了看这位35岁的新晋议员,摇了摇头。精明的外交官知道,历史的行程终归是阻挡不了的。
1982年5月8日,麦理浩在市民的欢呼声中最后一次在爱丁堡广场检阅了仪仗队,随后乘坐飞机回到了他阔别十年的故乡。
两年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双方在北京签订了《联合声明》,正式宣布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中国。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帷幕。
03
1986年12月,在北京主持香港贸发局驻京办事处开幕式的香港总督尤德爵士突发疾病去世。51岁的卫奕信“临危受命”,接任“港督”。这位英国政府中的“中国通”,曾经在香港大学学过中文,当过前港督柏立基爵士的政治顾问,用两年时间就通过了严苛的中文考试。
但是,这位新总督上任的第一年,就遭遇了世所罕见的大规模“股灾”。
关于这场股灾的细节,我们之前聊过(1987:破解“盛世股灾”的逃生之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人们普遍认为,导致这场股灾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了争夺拥有大量土地的企业,香港各大财阀掀起了激烈的“股市狙击战”。
1984年,“九七回归”已经板上钉钉,港府对房地产开发的热情大减,每年新增投入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被限制在五十公顷以下。这个时候,港岛的商业巨子们开始意识到,香港能够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日渐减少,大量并购拥有土地的企业将是一个不错的商机。
港府土地“断供”,房地产资本却开始急速膨胀。经历了“八七股灾”的震荡,香港百分之八十的工厂北移内地,直接对内地投资达到了140亿港元。而岛内的实业投资,纷纷转到了拔地而起的楼盘上。
香港经济结构变化的同时,陆港两地的资本交流也日渐频繁了起来。1986年,董家的“东方海外”船业公司开始渐渐萧条,入不敷出,甚至资金流也遭遇断裂的危险。那一年,来自大陆的资金通过霍英东打到了董先生账上,对于帮助这位“新船王”渡过难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像当时很多香港资本巨头一样,八十年代中后期,董先生与他的“东方海外”运输公司渐渐割断了与台湾方面的联系,挂上了五星红旗。
1992年,董建华决定弃商从政,担任了港英立法机关的“非官守议员”。1996年12月,按照《基本法》和《选举法》,“董先生”在选举委员会击败了三位竞争对手,正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为中国香港第一任特别行政长官。
▲1997年7月1日凌晨,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香港不再是“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97年7月1日,从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手中,“董先生”接过了这座海港城市几百万人生存、生活与发展的重担,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主掌这座城市的“本地人”。
历经整整三十年的艰难转型,当紫荆花旗与五星红旗同时高挂在维多利亚港的上空时,香港已经不再是殖民帝国遥远的边疆,而变成了深圳河对岸广袤而古老的祖国不可或缺的一个行政区。
从这一刻开始,他们不再是英王的“臣民”,而是现代祖国特别行政区的“公民”。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任行政长官,在七年的特首生涯里,董先生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昔日商界同侪的拥护和香港市民的拥戴。他击败了野心勃勃,“继承”前港英政府政策方针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统一了香港的行政权,抵御了金融风暴和房地产泡沫破裂对香港经济的冲击。
七年辛劳之后,2005年3月10日,在香港召开的记者会上,董建华正式提出,自己将辞任香港特首。
“由于长时期的操劳,在去年第三季度以后,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以香港的利益为重,我考虑过向中央提出辞任行政长官的请求,这是出于对香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我这些想法曾经向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过。”
那一天,董的语速不快,语调也很平和,但每一个字都仿佛惊天霹雳。放下讲稿,董建华轻轻拍打了几下自己的腿,笑着说道:再回答问题得搬个凳子来,因为自己已经站得很辛苦。
经过了七年多的辛劳,年近古稀的他宣读施政报告的时候都需要服用两片止痛药才能勉强站立。望着老人的背影,记者席上有人动情地喊道:“董生,保重。”
董先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面向香港数百万居民宣布辞职的行政长官。在殖民地的时代,总督的离职往往是通过任期届满英王政府不再发令延任实现的,即使辞职,也只是面向英王和英国政府。
这位香港历史上第一任特首,用他的离开宣示,回归后的香港与殖民地时代霄壤之别的地位。
两天后,中央政府接受了这位67岁的老特首的辞呈,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获任署理特首。
四十年前,面对咄咄逼人的总督戴麟趾和一众考官,那个只有中学学历的药品推销员也许不会想到,四十年后,自己将问鼎这座城市最高的权力宝座。
世事沧桑,历史大潮中每一个人都是见证者。
04
2005年6月21日,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内,曾荫权扎着领结,面对着国旗与监誓的总理,缓缓念出了誓词:
“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与出身“船王家族”的董建华相比,新任的“平民特首”曾荫权寄托了打破香港板结的政商权力巨网的希望。“世家”出身的董建华执政期间,港府一度成了一个“商人政府”,在人们心中,改变这一现状的重任已经落在了新任特首的肩上。
▲2007年,继任特首曾荫权竞选时的口号:“我会做好呢份工”
但七年后,曾荫权即将卸任之际的2012年2月10日,这位“平民特首”却被抓拍到在澳门的豪华赌场与“赌厅人士、贵利集团中人、夜总会从业员及多名黑道社团猛人”一同参加春茗,香港地产大亨刘銮雄、传媒大亨何柱国也坐在特首身侧,谈笑甚欢。
随后,曾的私人飞机、游艇、为退休后生活准备的豪华公寓、千支顶级红酒和收受各路商业大亨的礼物也被媒体毫不留情地披露报端。人们失望地发现,这位“平民特首”早已沦为了金钱与虚名的“猎物”。
2012年7月1日,曾荫权正式卸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席行政长官。两天后,BBC中文网上,评论员黄伟国评价,这是一份属于他的“分外落寞的黄昏”。等待他的,不再是安宁祥和的退休生活,而是漫长的刑事起诉,使他颜面扫地的刑事判决和无休无止的争议。
不过,值得瞩目的是,曾荫权是第一位由香港人自己问责的行政长官。1974年,刚刚成立的香港廉政公署将英国总警司葛柏从英国带回香港,送上了香港的法庭,当时全港为之一振。但是当总督本人面临指控的时候,问责他的却只能是“女王和她的政府”。
1992年,港督卫奕信面临着滥用香港财政预算的指控,最终以英方不再续任其港督职位而收场。而二十年后,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曾荫权则坐上了香港的审判庭。在香港地方法规的裁判之下,领受了自己应得的刑罚。
2019年1月,白发苍苍的曾荫权走出医院的羁押病房,正式重获自由。
“董先生”离开时前所未有的“体面”和曾先生走出医院时落魄的白发,共同书写了属于这座城市的希望。
诚然,走出漫长的殖民社会,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这个身份上的转换对每一个香港人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对于宏大历史中的个人来说,每一个向前迈进的脚步都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消化。
更何况,意识形态的差异,文化的异同和长达五十年的东西方“冷战”,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接受新的身份谈何容易。不解、彷徨,乃至用当年看待殖民者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同胞,对于走过这段艰辛长路的香港人来说,可能不够明智,但绝谈不上“愚蠢”。
如果把历史伤口漫长的弥合过程中的心理阵痛理解为“愚蠢”,站在道德高地上对自己的同胞横加辱骂,只能把双方之间的鸿沟越挖越深,让历史的伤口不断流出殷红的血液。
“解殖”与“进步”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两面,而不是针锋相对的“两阵”。当狂妄的评论者对这片土地居高临下地打上“愚蠢”的标签的时候,镜子中看到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滴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这份尊严同属于深圳河的两岸,而把偏见与仇恨倾注在自己同胞身上,将对方视为寇仇的姿态,与他们笔下那些用来以偏概全地攻讦同胞的,举着殖民地时代旧旗帜的跳梁小丑又有什么区别呢?
1939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刚刚燃起。维特根斯坦与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泰晤士河边散步,他们聊起了一则新闻:德国指责英国方面策划了一起针对希特勒的暗杀。维特根斯坦对此毫不惊讶,但马尔康姆却说:这种不够“文明正派”的行动与英国的“国民性格”格格不入,所以他绝不相信这样的传言。
维特根斯坦从此与这位学生断绝了来往。
五年后,在太平洋战场上服役的马尔康姆终于收到了维特根斯坦的来信,在信中,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向自己曾经的学生解释了导致他俩决裂的那场争论症结所在:
“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简单幼稚得令人吃惊。我发现研究哲学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并没有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
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样,希望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偏见掩盖了历史巨变的恢弘与沧桑,它让我们目眩于眼前的对抗与冲突,而错失了对美好未来的孜孜追求。
历史的明天,永远属于向前看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