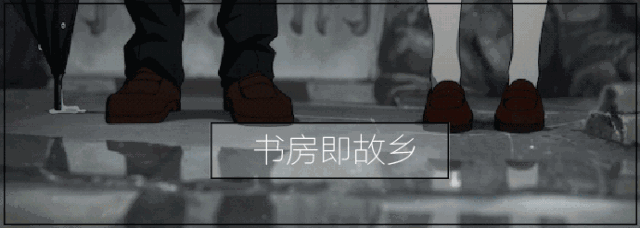
问题的提出发生在1970年夏日的某一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大约20个女性坐成一圈,尝试建立一个以增强意识为目标的小组。
只有几位女性举起了手。
事实上,可能很多女性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

在如今社会大谈女性权益和性别问题的舆论盛宴中,为什么女性在性爱中的欢愉未被谈起?女性为什么假装?又为什么隐藏?
表面上看,答案似乎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个方面:出于好意的迎合,或是为了保证自己始终处于被爱的角色。其实,进而言之,所有的这些为了保护和确认亲密关系的做法都可视为一种“欺骗”。但这种“欺骗”指向的是对“真实状态”的隐瞒,而非一种价值批判。因为它是我们从社会经验中习得的“有效”方法,假装性高潮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伴侣间的又一种情趣。
但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当女性假装性高潮成为一种潜在的性别规则,而女性开始质疑自己否是“正常”(因为没有性高潮觉得不正常)的时候。它成为一条存在于两性之间、社会与个人中不可忽视的裂痕。
那么,为什么我们无法认真对待假装高潮,以及夸张或者否定性欲的行为?美国著名女性心理学家哈丽特·勒纳(Harriet Lerner)通过三十余年心理治疗经验和大量真实案例说明,性高潮包含了欲望、社会建构、自由与开放等一系列话语,在不敢表达的女性身上,更需要一番认真的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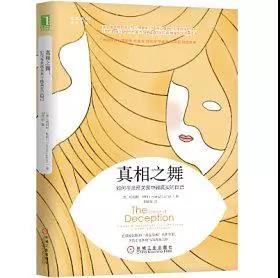
选自《真相之舞》,作者哈丽特·勒纳博

《她/HER》 剧照
01
假装,和呼吸一样自然
当时,假装性高潮让我觉得只是一个女性常识。我们的文化传统教导女性这样做,来吸引并留住男人,维护男人的尊严,夸大男人的尺寸,无论他说的话多么无聊都要无辜地睁大眼睛去聆听。
我从小就学会了如何在男人面前假装。这种假装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像礼仪礼节一样普通。在布鲁克林读六年级的时候,老师建议我们给男生写信的时候要故意拼错几个词,这些会显得比较可爱,我认真地记住了这个建议,甚至在写信之前会查字典以确保我拼错了单词。
我的老师当年的建议现在看来或许很蠢,但它却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前女性主义教学思潮,它要求女性要耍点小聪明来抓住男人的心,同时还要小心不要表现得比男人更聪明。女性需要装得弱不禁风、脆弱无助而又小鸟依人,当然如果这些是与生俱来的气质,那她就非常幸运了。
有这样一位研究受欢迎的女性的专家阿莲妮·达尔,她的书《永远征询男性的意见》(Always Ask a Man)中这样写道:
一位成功的女性永远不会将她的能力和她的性别置于对立面。永远不要抢男人的风头。不要显得比男人更加风趣幽默,即便你有很好的笑话,也要咬住舌尖不要开口。
不要就某一个话题大声说出你的观点……而要引出男人的观点,然后偶尔给他们的想法优雅地加上注解。如果你抽烟,不要随身带火柴。
在餐厅里要让你的同伴或约会对象来点餐。你可能比餐厅的服务生更懂葡萄酒,但如果你够聪明,你就要让男人来选酒,就算他最后选的葡萄酒喝起来像肥皂水,你也要装出被折服的样子。

《她/ELLE》 剧照
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假装获得性高潮这件事,在我看来和以上这些做法没什么本质区别,也并不比咬自己的舌头或者喝肥皂水一样的葡萄酒更可怕(可见女性的“消极”对她们无疑是一种虐待)。我觉得这些行为只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标签,我也是她们中的一员,只是一旦恋爱关系结束,我们就会像蜕去蛇皮一样甩开这些假装。
对于这种教育背后自相矛盾的种种规则及其强大的潜意识力量,我实在无法表现出欣赏的态度。这些规则教我们削弱自己的力量,来增强男人的力量和我们与男人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对于男人来说,就是不守女人的本分、不可爱、具有毁灭性,甚至是一种生命威胁。
而我们往往对这些规则太过烂熟于心,以至于除了面对那些需要被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或经济实力的男人(比如丈夫或者老板)之外的时候,我们还会不由自主地将它适用于我们其他重要的人际关系中,比如和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母亲、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的伴侣……
我从没想过,当我们不展现出真实的自我的时候,对自己以及男人们的生活会造成可怕的影响,用卡罗琳·海莉布朗的话来说,我们都在扮演“模拟女性”。

《革命之路》 剧照
02
女孩,连“阴蒂”这个词都说不出
作为她新的心理咨询师,22岁的大学毕业生克里斯塔,说自己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告诉我,并且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她说自己已经隐瞒这个秘密多年,而它带来的深深羞耻感只是有增无减:
除非她持续刺激自己的阴蒂,否则她无法在性爱时候达到高潮。
让我更感疑惑的是,她对于简单需求的羞耻感。为什么无论是对她身边的人、她的男性伴侣甚至是她的好闺蜜们,她都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
最简单的原因,她觉得自己是全加利福尼亚、全美国甚至全世界唯一一个不刺激阴蒂就无法在性爱中获得高潮的女人。她就是这样的人,她在和自己深爱的伴侣做爱时会假装高潮,因为不这样做就会让这个美好的过程大打折扣。克丽丝塔解释道:“如果我告诉他我没有高潮,那会毁掉那种气氛。”她还害怕会失去他,他会转而选择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可以直接获得高潮的女人。
其次,克丽丝塔羞于说出“阴蒂”这个词,好在她最终在我面前说出来了,而在此之前,这个单词从未在她的口中出现过。她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词应该如何发音,也没有人告诉过她她有一个部位叫作“阴蒂”。大家对这个部位的闭口不谈给了她一种错觉:这个能够集中代表她的性别的身体部位,是被禁止谈论的,甚至是奇怪的、可笑的。

《她/ELLE》 剧照
在20世纪70年代,心理分析学家普遍认为,这种感觉反映出的是女人的“阴茎嫉妒”,但在我并不同意我同事说的克丽丝塔潜意识里是在渴望拥有阳具的时候,我没有说出来。我认为克丽丝塔渴望的,是自己的女性身份的认同。她最想要的是做自己。
那时,我开始明白那么多女性在性爱中假装高潮(或者假装对性爱有极高的热情)的深层原因:我们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让女性更在意自己让别人获得的快感,而不是自己的体验。假装性高潮是女性的自我欺骗的重要例子之一,她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的性伴侣得到鼓舞,也保护他们的尊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已经将男人需要从女人那里获得的东西深深烙印在了心里,并且坚信他们有权利得到这些东西。

《女性瘾者》 剧照
克丽丝塔“假装高潮”的案例和她自己的态度也有关系,她没有将阴蒂看作自己性器官的一部分。她的沉默和欺骗行为,不仅仅反映出她对此神经敏感,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女性生殖器官普遍的错误认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还盛行一时。比如在心理治疗师业内,我的很多同事仍然将阴蒂看作成年人性征中发育不全的一个器官,偏好阴蒂高潮而非阴道高潮的女性会被贴上“男性化”或“阴茎崇拜”(就好像我们中有人想要成为数学家或工程师一样)的标签,并且被认为她们从中表达的是“对阳具的嫉妒”或“性不成熟”。虽然马斯特和约翰森在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问问我们女性呢?),弗洛伊德的传统观念仍然占据了上风。专家们认为阴蒂不是性征的重点,甚至不属于性征的一部分,于是克丽丝塔也这样认为。
后来心理分析师们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但改变并不大。我们两腿之间的这个器官,仍然没有被主流文化给予一个恰当的名字,甚至仍然没有名字,而女性对此也很有默契地不发一言。也许这就是我们假装的开始。
03
是谁,决定了什么是正常的?
和克丽丝塔一起工作了那么久,我好像一直没有给她提供什么绝妙的见解,但我的确鼓励她要将这个秘密公开出来,她也的确这么做了。在她第一次公开说起这件事之后的第一次治疗,她告诉我她和自己的女性朋友们开诚布公地谈起了这个话题,然后发现几乎一半的女性都需要在性交中被刺激阴蒂从而获得高潮。我以为这意味着这里面的每一位女性都这么做了,或者通过什么别的方式达到了高潮,然而我错了。克丽丝塔告诉我,这些女性和她一样,都假装获得了高潮。“我松了一口气,”克丽丝塔告诉我,“原来这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问题。”
“你说的问题是什么?”我问道。
“当然是我们不能正常地获得高潮。”克丽丝塔回答道,仿佛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
“是谁决定了什么才是正常呢?”我追问道。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那次谈话,因为就是那时我发现,在女性心理面前,“科学的沟通”都不过是在和她们的心理“兜圈子”。一旦某样东西被定义为“非女性化的”或者“不适合这个性别的”,我们就很难去改变这个规则了。一旦哪个女性的举止和规定的不太一样,那么这个例外只会证明规定,而不会令大家质疑规定,而这个女性自然会被另眼看待。女性们仍然在调整自己,让自己靠近规定里女性的样子,而不是成为自己本来的样子。

《她/ELLE》 剧照
也许是因为我当时才刚刚进入心理治疗行业,我感觉自己没有给克丽丝塔多大帮助。无疑更多的是她激发了我的思考,而不是我激发她。但她的女性朋友们却在性高潮的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她们开始问:“是谁说的?”
是克丽丝塔的女性朋友们帮她重命名了她的问题—它并非起源于个人的异常,而是源于克丽丝塔所无条件接受的错误性观念。很快,克丽丝塔不再担心自己有什么病,但她说出了新的困境:她是否应该诚实面对自己的男友,告诉他自己的性需求,即使冒着他会因此疏远自己的危险?又或者她是不是应该继续假装高潮,维持现状?克丽丝塔选择了后者。
那是1970年,对我和克丽丝塔来说,女性运动才刚刚开始。
04
无辜的假装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假装性高潮并非不道德的事情(相对于否认婚外情来说),而这种假装也没有被看轻。像“假装”“伪造”和“捏造”这些词,总是难免显得轻飘飘的,它们会让人想到谨慎的、女性化的举止,甚至是礼貌的举止。女性们仍然告诉我,在她们看来假装高潮是一件没有恶果的事情,而只是一件女人们都会做的事情,她们这么做的时候也没有恶意。我母亲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有些妇产类的文章还会建议医生指导他们的病人去假装性高潮,因为为了满足女性取悦丈夫的愿望,没有其他比这些“善意的欺骗”或“善意的激励”更合适的了。很多女性根本没有意识到,她们的身体和性器官是为了她们自己而存在的,她们应该是为自己而活的。
为什么“撒谎”和“假装”这两个词给我们的感觉这么不一样?在我们眼里,撒谎是一种自私自利、自我保护的行为,而假装则相反可能是在损己利人。举个例子,性爱过程中不同的假装,它们甚至影响着社会文化规则,以至于我们的文化开始要求女性在床上顺从男性,他们想听到什么,就能听到什么。
因此,“现代女性”会假装高潮,而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则会否认性快感的存在,强大的文化压力使得她们不得不在性爱过程中抑制自己的本能,扮演一个沉睡的白雪公主。类似的还有从古至今的女性都一致否认她们对其他女性的肉欲和感觉,她们的性自由(和异性的)也是有限的,因为她们被告知不要行使这种自由。在高中和大学时期,我受到的教育就是:有欲望是正常的,但我不应该主动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因为那是在婚前对自己的“滥用”,婚前性行为会降低我的价值,在那些吹捧贞洁的男人中失去市场。当然了,还是一直有勇敢的女性反抗着这些社会的非难,她们拒绝和这个社会的文化同流合污,她们不相信男人对她们说的有关她们的话,她们坚持真实地活着,无论是性方面还是其他什么方面,都活得真实。

《年轻女子》 剧照
为什么我们会最小化自我背叛行为的负面影响,甚至把它归于女性的美德?为什么我们无法认真对待假装高潮、夸张或否定性欲的行为?为什么我们会欣然接受自己最私密的部位连一个名分都没有这种事情?纵观世界史,女性并不是简单地出于好意而“假装”,而是被迫在床上向男人撒谎,以保证自己被爱。“性欲强烈”的修女和“难以取悦”的妻子可能曾接受过阴蒂切除术,不忠的、选择脱离男性控制的妻子(尤其是那些后来变为同性恋的女性)可能曾是笑柄、曾是家庭暴力的对象。有很多已婚的女人宁愿一个人睡,但她们在床上的谎言是一种经济和感情上的需要,因为性生活仍然被看作是丈夫的权利、妻子的义务。而对很多人来说,即使眼下没什么需要保护的东西,但假装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们有时候意识不到我们在因为恐惧而在演戏,甚至有时都意识不到自己在演戏。从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愉悦时,我们就接收不到身体的任何信号了,无论是性欲高涨的信号,还是冷淡的信号。取而代之的是疲惫感和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不想要”。我们也许还是会尝试去“寻找状态”,但“做爱”的时候却在想着些别的人和事。我们习惯性地还在演戏,这种行为已经是条件反射、无须大脑思考的了。
当然,将所有的撒谎都定义为“为自己”,而将演戏都定义为“为了别人”,有点过于简单粗暴了。除非我们不再撒谎,也不再演戏,否则要对这两者进行区分,是很困难的。因为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出我们的谎言保护了谁,保护了什么。撒谎和假装的开始,往往是因为我们处于一种焦急或受威胁的境地中,我们急切地想要改善这种状况。
所以克丽丝塔的假装高潮不只是“为了他”,更是一种“留住他”的策略。她想要保护他的感情不受伤害,也想避免面对他受伤的感情。另外,克丽丝塔也可能受到对于性和亲密关系的忧虑的阻碍,因此她无法在床上坦然面对男友。但她演的戏不一定真的“对他好”,因为一旦她的男友发现自己被骗了,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不那么真实,他可能会震惊不已,甚至怒火中烧。
长久以来,无论是在卧室还是在会议室里,女性的工作都是夸赞男人,让他们的形象比实际上更伟大。早在1929年,弗吉尼亚·沃尔夫就在她的《一个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提到过,女性之所以显得地位较低,和她们始终扮演的放大男人形象的角色是有关系的。

《女性瘾者》 剧照
因为如果她开始实话实说,镜子里的影像就会缩小,他的生命活力就被削弱了。如果不能在早晚餐的时候看到自己伟大的形象(是他实际的两倍大),他还怎么继续评判事物、教化当地人、制定法律、写书、穿衣,和在宴会上发表演讲?
克丽丝塔有一次提到说,她在扮演一个完美的情人,这样来让她的男朋友感觉到他也是一个完美的情人。克丽丝塔的假装显然是有所企图的,虽然她的方向有所偏差,但她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她的尊严,也保护他的尊严。在这样一个没有给真正的、多样的女性感受正名的文化背景下,克丽丝塔是在屈从于主流文化关于“一个真正的女人”应该感觉到什么、应该怎么做的规定。她在尝试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和“别的女人”一样的女人,因为就她所知她的感受是不对的、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不够好的—又或者她连自己真实的感觉是什么都不知道。